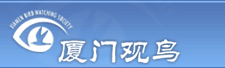2007-01-07 03:18 2007-01-07 03:18
ķōŠµÄź:
#1
|
|
|
µÖ«ķĆÜõ╝ÜÕæś    ń╗äÕł½: µŁŻÕ╝Åõ╝ÜÕæś ÕĖ¢ÕŁÉ: 803 µ│©Õåī: 2005-08-24 ń╝¢ÕÅĘ: 970 |
õĖĆÕŬķĖ¤’╝īµ»öÕ”éńö╗ń£ēÕɦ’╝īÕż®Õż®µöŠÕŻ░ÕĢ╝Õö▒’╝īÕŻ░ķ¤│ÕɼµØźµĆ╗µś»ķéŻõ╣łµĖģõ║«µé”ĶĆ│ŃĆ鵳æõ╗¼µÖ«ķĆÜõ║║Õł░KÕÄģÕÉ╝õĖƵÖÜõĖŖµŁī’╝īµł¢ĶĆģĶĆüÕĖłĶ┐×Ķ«▓ÕćĀÕĀéĶ»Š’╝īÕŚōÕŁÉÕ░▒õĖŹÕģŹÕÅśÕŠŚÕÅæÕōæŃĆ鵳æõ╗¼µ£ēÕÅ»ĶāĮµŗźµ£ēÕāÅķĖ¤Õä┐ķ鯵ĀĘńÜäĶłīÕż┤ÕÉŚ’╝¤ÕŻ░ńÄ»µø▓ĶĆüÕĖłńÜäõ╣”ŃĆŖÕŚōķ¤│ńÜäń¦æÕŁ”Ķ«Łń╗āõĖÄõ┐ØÕüźŃĆŗ’╝łķÖäµ£ēõĖżÕ╝ĀµĢÖÕŁ”ńż║Ķīā VCD’╝ē’╝īÕÅ»õ╗źµÅÉõŠøõĖĆõĖ¬Ķé»Õ«ÜńÜäńŁöµĪłŃĆ鵣żõ╣”õ╗Ä2005Õ╣┤1µ£łÕć║ńēł’╝īĶć│2006Õ╣┤10µ£ł’╝īÕĘ▓ń╗ÅÕŹ░ÕłĘÕøøµ¼ĪŃĆéÕŻ░ńÄ»µø▓ĶĆüÕĖłńÜäĶ┐ÖÕźŚµ¢╣µ│Ģ’╝īõ╣¤ÕĘ▓ń╗ÅķĆĀń”Åõ║åÕŠłÕżÜõ║║õ║åŃĆéńÄ░Õ£©Õź╣ÕćåÕżćĶĄĀõĖƵ£¼ń╗ÖķĖ¤õ╝ÜńÜäÕøŠõ╣”Õ«ż’╝īń£¤µś»Õż¬ÕźĮõ║åŃĆéķĖ¤õ╝ÜńÜäĶĆüÕĖłõĖŹÕ░æ’╝īńł▒KµŁīńÜäõ║║ÕźĮÕāÅõ╣¤µī║ÕżÜ’╝īµŁŻÕźĮķāĮńö©ÕŠŚńØĆŃĆ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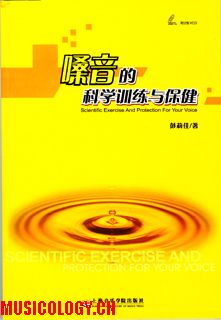
ÕŻ░ńÄ»µø▓ĶĆüÕĖłµś»Õ╣┐ÕĘ×µś¤µĄĘķ¤│õ╣ÉÕŁ”ķÖóµĢֵij’╝īÕĤµ£¼ÕŹ┤µś»õĖŁµ¢ćń│╗Õć║Ķ║½’╝īÕøĀÕ»╣ķ¤│õ╣ÉńÜäńŚ┤ńł▒ĶĆīĶ┐øÕģźĶ┐ÖõĖ¬õĖōõĖÜķóåÕ¤¤ŃĆéÕź╣õĖŁµ¢ćÕ║ĢÕŁÉµĘ▒ÕÄÜ’╝īµĢÖÕŁ”õ╣ŗõĮÖ’╝īÕģ╝ÕüÜķ¤│õ╣ÉÕłŖńē®ńÜäń╝¢ĶŠæŃĆéÕź╣ńÜäµ¢ćÕŁŚń╗ÖµłæńÜäµä¤Ķ¦ē’╝īµś»µ¢®µł¬ĶĆīÕł®ĶÉĮ’╝īńö¤ÕŖ©ĶĆīµśÄÕ┐½ŃĆéĶ»┤Õł░µłæĶĘ¤ÕŻ░ńÄ»µø▓ĶĆüÕĖłńÜäĶ«żĶ»å’╝īõ╣¤Ķ«ĖĶ┐śĶ”üµŗ£ķĖ¤õ╣ŗĶĄÉŃĆéµ£ĆĶ┐æµłæķćŹÕø×õĖĆõĖ¬ÕćĀÕ╣┤ÕēŹµĄüĶ┐×Ķ┐ćńÜäÕÅżÕģĖķ¤│õ╣ÉĶ«║ÕØø’╝īÕ£©Õē»ńēłń╗ÖķéŻķćīńÜäµ£ŗÕÅŗĶ┤┤ÕøŠõ╗ŗń╗ŹķĖ¤ń▒╗’╝īÕŻ░ńÄ»µø▓ĶĆüÕĖłõĖŹõ╗ģń╗Öõ║łńāŁµāģÕø×ÕżŹ’╝īĶĆīõĖöµĀ╣µŹ«µłæńÜäķōŠµÄź’╝īķĪ║ĶŚżµæĖńō£µØźÕł░õ║åµłæõ╗¼ķĖ¤õ╝ÜŃĆéÕŻ░ńÄ»µø▓ĶĆüÕĖłÕÅ»Ķ░ōµĆ¦µāģõĖŁõ║║’╝īõĖŗķØóµłæµ£¬ń╗ÅÕź╣ÕÉīµäÅ’╝īĶ┤┤õĖƵ«ĄÕź╣µØźõ┐ĪõĖŁńÜäĶ»Ø’╝Ü µłæńÜäõ╣”õĖĆÕ╝Ćń»ćÕ░▒õ╗źķĖ¤õĮ£Õ╝ĢÕŁÉŌĆöŌĆöŌĆ£õ║║õ╗¼ÕŠĆÕŠĆõĖĆÕÉ¼Õł░ķ╗äĶÄ║ńÜäķĖŻÕŽÕ░▒Õ¢£õĖŹĶć¬Ķā£’╝īÕ╝éÕÅŻÕÉīÕŻ░ĶĄ×ńŠÄÕ«āµś»ŌĆ£µŁīÕö▒Õ«ČŌĆØ’╝øĶĆīõĖĆÕÉ¼Õł░õ╣īķĖ”ńÜäÕŻ░ķ¤│ÕŹ┤ÕÄīńā”õĖŹÕ«ē’╝īńöÜĶć│µüɵā¦ŃĆüÕÆÆķ¬é’╝īµ»½µŚĀµØźńö▒Õ£░µīćĶ┤ŻÕ«āÕś┤ÕĘ┤õĖŹÕÉēÕł®ŃĆéõ╗öń╗åµā│õĖƵā│’╝īķ╗äĶÄ║ÕüÜõ║åÕżÜÕ░æÕźĮõ║ŗ’╝¤õ╣īķĖ”ÕÅłÕüÜķöÖõ║åõ╗Ćõ╣ł’╝¤ŌĆ”ŌĆ”ŌĆصłæńøĖõ┐Ī’╝īÕåźÕåźõ╣ŗõĖŁ’╝īÕĘ▓ń╗ŵ│©Õ«Üõ║åµłæĶʤõĮĀõ╗¼ķĖ¤õ╝ܵ£ēń╝śńÜäŃĆ鵳æńł▒õĮĀõ╗¼ńÜäķĖ¤õ╝Ü’╝īńł▒ķĖ¤õ╝ÜõĖŁµēƵ£ēµ£ŗÕÅŗ’╝üõ╗ŖÕÉÄĶŗźµ£ēń▒╗õ╝╝õĮĀõ╗¼õĖŖµ¼ĪĶ┤ĄÕĘ×Ķ¦éķĖ¤ķ鯵ĀĘńÜäµ┤╗ÕŖ©’╝īµłæõĖĆÕ«Üõ║ēÕÅ¢ÕÅéÕŖĀŃĆ鵳¢ĶĆģ’╝īÕ”éµ×£ķĖ¤õ╝ÜõĖŁńÜäĶĆüÕĖłõ╗¼µ£ēķ£ĆĶ”ü’╝īõĖŗÕŁ”µ£¤µłæõ╣¤ÕÅ»õ╗źµŖĮµŚČķŚ┤Ķć¬Ķ┤╣ÕÄ╗ÕÄ”ķŚ©Ķ«▓Ķ»ŠŃĆ鵳æńÜäĶ»Šµś»ÕŠłń▓ŠÕĮ®ńÜä’╝īµłæõ╗Ŗńö¤µ£ĆÕŠŚµäÅńÜäõĖżõ╗Čõ║ŗÕ░▒µś»’╝ÜõĖĆŃĆüÕ░åõĖÜõĮÖńł▒ÕźĮńÄ®µłÉõ║åõĖōõĖÜÕ╣ȵē®Õż¦õ║åĶ»źõĖōõĖÜńÜäÕ║öńö©ķØó’╝øõ║īŃĆüĶ»ŠĶ«▓ÕŠŚÕŹüÕłåµĮćµ┤ƵĄüńĢģ’╝īĶ«®Õɼõ╝Śõ╗źµ×üĶĮ╗µØŠµ×üÕ┐½õ╣ÉńÜäµ¢╣Õ╝ÅÕŠŚÕł░µ×üµ£ēµĢłńÜäµīćÕ»╝ŃĆé -------------------- õĮĀõ╗¼ń£ŗķéŻÕż®õĖŖńÜäķŻ×ķĖ¤’╝īõ╣¤õĖŹń¦Ź’╝īõ╣¤õĖŹµöČ’╝īõ╣¤õĖŹń¦»ĶōäÕ£©õ╗ōķćī’╝īõĮĀõ╗¼ńÜäÕż®ńłČÕ░ÜõĖöÕģ╗µ┤╗Õ«āŃĆéõĮĀõ╗¼õĖŹµ»öķŻ×ķĖ¤Ķ┤ĄķćŹÕŠŚÕżÜÕÉŚ’╝¤õĮĀõ╗¼Õō¬õĖĆõĖ¬ĶāĮńö©µĆØĶÖæõĮ┐Õ»┐µĢ░ÕżÜÕŖĀõĖĆÕł╗Õæó’╝¤õĮĢÕ┐ģõĖ║ĶĪŻĶŻ│Õ┐¦ĶÖæÕæó’╝¤õĮĀµā│’╝īķćÄÕ£░ķćīńÜäńÖŠÕÉłĶŖ▒µĆÄõ╣łķĢ┐ĶĄĘµØź’╝īÕ«āõ╣¤õĖŹÕŖ│Ķŗ”’╝īõ╣¤õĖŹń║║ń║┐’╝īńäČĶĆīµłæÕæŖĶ»ēõĮĀõ╗¼’╝ÜÕ░▒µś»µēĆńĮŚķŚ©µ×üĶŹŻÕŹÄńÜ䵌ČÕĆÖ’╝īõ╗¢µēĆń®┐µł┤ńÜäĶ┐śõĖŹÕ”éĶ┐ÖĶŖ▒õĖƵ£ĄÕæó’╝üõĮĀõ╗¼Ķ┐ÖÕ░Åõ┐ĪńÜäõ║║Õō¬’╝īķćÄÕ£░ķćīńÜäĶŹēõ╗ŖÕż®Ķ┐śÕ£©’╝īµśÄÕż®Õ░▒õĖóÕ£©ńéēķćī’╝īńź×Ķ┐śń╗ÖÕ«āĶ┐ÖµĀĘńÜäÕ”åķź░’╝īõĮĢÕåĄõĮĀõ╗¼Õæó’╝¤ ŌĆöŌĆöŃĆŖķ®¼Õż¬ń”Åķ¤│ŃĆŗń¼¼ÕģŁń½Ā
|
 |
Õø×ÕżŹ
 2007-01-31 05:55 2007-01-31 05:55
ķōŠµÄź:
#2
|
|
|
µÖ«ķĆÜõ╝ÜÕæś    ń╗äÕł½: µŁŻÕ╝Åõ╝ÜÕæś ÕĖ¢ÕŁÉ: 803 µ│©Õåī: 2005-08-24 ń╝¢ÕÅĘ: 970 |
ÕźĮÕɼĶĆÉÕɼ µ¢╣õĖ║µŁŻķĆö
ŌĆöŌĆöõĖÄķś┐ķĢŚĶ░łõĮ£µø▓ ÕŻ░ńÄ»µø▓ Õ£©ŌĆ£ńł▒õ╣Éõ║║ķÜÅń¼öŌĆØńĮæń½Ö’╝īń£ŗÕł░ÕÅ░µ╣ŠõĮ£µø▓Õ«Čķś┐ķĢŚĶ░łõ╗¢Ķć¬Ķ┤╣ÕłČõĮ£ŃĆüÕÅæĶĪīŃĆŖńź×ķøĢõŠĀõŠŻõ║żÕōŹõ╣ÉŃĆŗ’╝īÕÄåÕ░ĮĶē░Õø░ńÜäÕĖ¢ÕŁÉ’╝īķĪ┐ńö¤ÕźĮÕźćõ╣ŗÕ┐āŃĆéŌĆ£EŌĆØµØźŌĆ£EŌĆØÕŠĆõĖĆńĢ¬ÕÉÄ’╝īÕÅæńÄ░õ╗¢ÕĤµØźµś»µłæńÜäÕĘźõĮ£ÕŹĢõĮŹŌĆöŌĆöµś¤µĄĘķ¤│õ╣ÉÕŁ”ķÖóńÜ䵌®µ£¤µĀĪÕÅŗŃĆéõ║ĵś»’╝īĶÉīńö¤õ║åŌĆ£EŌĆØĶ«┐õ╗¢ńÜäÕ┐ĄÕż┤ŃĆéõ╗źõĖŗ’╝īµś»ŌĆ£EŌĆØĶ«┐ńÜäµĢ┤ńÉåń©┐ŃĆé ÕĮŁ’╝ܵłæÕÅæńÄ░õĮĀńÜäõĮ£ÕōüõĖŹõĮåķćÅÕżÜĶ┤©ķ½ś’╝īµČĄńø¢õ║åńŗ¼Õö▒ŃĆüÕÉłÕö▒ŃĆüńŗ¼ÕźÅŃĆüķćŹÕźÅŃĆüÕÉłÕźÅŃĆüÕŹÅÕźÅµø▓ŃĆüõ║żÕōŹĶ»ŚŃĆüõ║żÕōŹõ╣ÉŃĆüµŁīÕē¦ńŁē’╝īĶĆīõĖöÕŠŚÕł░ĶĪīÕ«ČńÜäÕŠłķ½śĶ»äõ╗ĘŃĆéĶ┐×ńź¢ÕĖłńłĘń║¦ńÜäĶ«ĖÕŗćõĖēŃĆüÕ╝ĀĶé¢ĶÖÄŃĆüµØÄńäĢõ╣ŗńŁēÕēŹĶŠłķ½śõ║║’╝īńö¤ÕēŹķāĮÕ»╣õĮĀµÄ©Õ┤ćµ£ēÕŖĀŃĆéĶ»ĘķŚ«’╝īõĮĀµś»µĆÄõ╣łÕüÜÕł░ńÜä’╝¤ ķĢŚ’╝ÜÕģČÕ«×’╝īµłæÕŬµś»õĖ¬õĖÜõĮÖõĮ£µø▓Õ«ČŃĆ鵳æńÜäõĖōõĖܵś»Õ░ŵÅÉńÉ┤µĢÖÕĖłŃĆéõĖŹĶ┐ć’╝īÕćĀÕŹüÕ╣┤µØź’╝īµłæµŖĢµ│©Õ£©õĮ£µø▓õĖŖńÜ䵌ČķŚ┤ŃĆüÕ┐āÕŖøŃĆüķćæķÆ▒’╝īÕ╣ČõĖŹµ»öõĖĆĶł¼õĖōõĖÜõĮ£µø▓Õ«ČÕ░æŃĆéÕøĀõĖ║µś»õĖÜõĮÖ’╝īµēĆõ╗źõĖŹÕ┐ģńÉåõ╝ÜŌĆ£µĮ«µĄüŌĆØ’╝īÕŬÕåÖĶć¬ÕĘ▒µā│ÕåÖŃĆüńł▒ÕåÖńÜäõĖ£Ķź┐ŃĆéńē╣Õł½Õ╣ĖĶ┐ÉńÜ䵜»’╝īõĖĆńø┤ķüćÕł░ń¤źķ¤│ÕźĮÕÅŗ’╝īÕÅłÕ«×ĶĪīõ╗źńÉ┤Õģ╗µø▓ńÜäŌĆ£ńŁ¢ńĢźŌĆØ’╝īń║”õĖĆÕŹŖńÜäõĮ£ÕōüķāĮĶó½µ╝öÕć║Ķ┐浳¢ńüīÕĮĢõ║åCD’╝īĶ┐×µ£ĆķÜŠµ£ēµ╝öÕć║µ£║õ╝ÜńÜ䵣īÕē¦ŃĆŖĶź┐µ¢ĮŃĆŗ’╝īõ╣¤µøŠÕ£©ÕÅ░µ╣ŠĶ┐×µ╝ö8Õ£║ŃĆéµ£ĆĶ┐æ’╝īµłæÕÅłĶć¬Ķ┤╣ÕłČõĮ£Õć║ńēłõ║åŃĆŖńź×ķøĢõŠĀõŠŻõ║żÕōŹõ╣ÉŃĆŗŃĆéõĖĆõĖ¬õĮ£µø▓Õ«Č’╝īĶāĮÕ£©µ£ēńö¤õ╣ŗÕ╣┤ń£ŗÕł░Ķć¬ÕĘ▒ńÜäõĮ£Õōüµ╝öÕć║ŃĆüÕć║ńēł’╝īµś»Õż¦Õ╣ĖŃĆé ÕĮŁ’╝ܵłæÕÅŹÕżŹĶüåÕɼõĮĀńÜäŃĆŖńź×ķøĢõŠĀõŠŻõ║żÕōŹõ╣ÉŃĆŗ’╝īĶ¦ēÕŠŚÕģźĶĆ│ŃĆüÕģźÕ┐āŃĆüõ║½ÕÅŚŃĆüµä¤ÕŖ©’╝īķĆÜĶ║½ĶłÆńĢģŃĆéµ»ÅÕø×ĶüåĶĄÅ’╝īµłæķāĮµāģķÜŠĶ欵Ŗæ’╝īµä¤Ķ¦ēõ║öĶäÅÕģŁĶģæõ╣āĶć│Õģ©Ķ║½µ»ÅõĖ¬ń╗åĶā×ķāĮÕ╝ĀÕ╝ĆµØźµĘ▒Õæ╝ÕÉĖŃĆéµ£ēµŚČµłæõ╝ÜÕ┐ĮķŚ¬ńüĄµā│’╝ÜĶ┐Öµś»ÕÉ”Õ░▒µś»ŌĆ£ńüĄķŁéÕć║ń¬ŹŌĆØńÜäÕɼõ╣ÉÕóāńĢī’╝¤ĶĆüÕ«×Ķ»┤’╝īĶ┐Öń¦Źµä¤Ķ¦ē’╝īÕżÜÕ╣┤µØźµ£¬µøŠµ£ēĶ┐ćŃĆéõĮĀĶāĮÕÉ”Ķ░łõĖĆĶ░łõĮĀÕåÖŃĆŖńź×õ╣ÉŃĆŗńÜäÕ┐āÕŠŚõĮōõ╝Ü’╝¤ ķĢŚ’╝ÜĶ┐Öµś»µłæõĖĆńö¤ĶĆŚµŚČµ£ĆķĢ┐ńÜäõĮ£ÕōüŃĆéõ╗ÄÕå│Õ«ÜÕåÖÕł░õ┐«Ķ«óÕ«īµłÉ’╝īµĢ┤µĢ┤ĶŖ▒õ║å28Õ╣┤ŃĆéĶ┐ÖõĖŁķŚ┤ńÜäµĢģõ║ŗÕż¬ÕżÜ’╝īõĖŹń¤źĶ”üõ╗ÄõĮĢÕżäĶ«▓ĶĄĘ’╝¤ ÕĮŁ’╝ÜÕ░▒õ╗ÄõĮĀõĖ║õ╗Ćõ╣łĶ”üÕåÖÕ«āÕ╝ĆÕ¦ŗÕɦŃĆé ķĢŚ’╝Üķ鯵ś»30Õ╣┤ÕēŹńÜäõ║ŗõ║åŃĆéÕĮōµŚČµłæÕ£©ķ®¼µĆØիŵĢֵijÕĖ«ÕŖ®õĖŗ’╝īĶĆāĶ┐øõ║åńŠÄÕøĮĶé»ńē╣ÕĘ×ń½ŗÕż¦ÕŁ”ķ¤│õ╣ÉńĀöń®ČµēĆŃĆéõĖĆÕż®’╝īń£ŗÕł░ÕÉīÕŁ”Õ£©ń£ŗķćæÕ║ĖńÜ䵣”õŠĀÕ░ÅĶ»┤ŃĆŖńź×ķøĢõŠĀõŠŻŃĆŗ’╝īõŠ┐ÕƤµØźń┐╗õĖĆõĖŗŃĆéµ▓Īµ¢Öµā│’╝īÕĮōÕ£║Ķó½Ķ┐ĘõĮÅŃĆéÕćĀõ╣ĵś»õĖĆÕÅŻµ░ö’╝īń£ŗÕ«īõ║åÕģ©ÕźŚõ╣ŗÕÉÄ’╝īµłæÕĮōÕŹ│ÕÅæµä┐’╝ܵ£ēńö¤õ╣ŗÕ╣┤’╝īõĖĆÕ«ÜĶ”üõĖ║Ķ┐Öķā©õ╣”ÕåÖõĖĆķā©õ║żÕōŹõ╣ÉŃĆé ÕĮŁ’╝Üõ╗Ćõ╣łõĖ£Ķź┐µä¤ÕŖ©õ║åõĮĀ’╝¤ ķĢŚ’╝ܵŚĀµ│ĢĶ»┤µĖģµźÜŃĆéÕÅ»ĶāĮµś»µØ©Ķ┐ćÕ░ŵŚČõŠ»ńÜäÕüŵ┐ĆŃĆüÕÅŹÕÅø’╝īĶ«®µłæĶüöµā│ĶĄĘĶć¬ÕĘ▒ńÜäķØÆÕ░æÕ╣┤µŚČ’╝øÕÅ»ĶāĮµś»µØ©Ķ┐ćõĖĆńŁēÕ░ÅķŠÖÕź│16Õ╣┤ńÜäõĖōµāģŃĆüń║»µāģ’╝īĶ«®Ķć¬ÕĘ▒Õ┐āµ£ēµłÜµłÜńäēŃĆéµĆ╗õ╣ŗ’╝īµś»Õ¤ŗĶŚÅÕ£©µ£ĆÕ┐āÕ║Ģķ鯵Ā╣Õ╝”Ķó½Ķ¦”ÕŖ©õ║åŃĆé ÕĮŁ’╝ÜõĖ║õ╗Ćõ╣łĶ”üÕåÖ28Õ╣┤ķéŻõ╣łõ╣ģ’╝¤ ķĢŚ’╝ÜÕåÖõ║żÕōŹõ╣É’╝īõĖŹµś»µā│ÕåÖÕ░▒ĶāĮÕåÖńÜäŃĆ鵳æµĘ▒ń¤źõ╗źĶć¬ÕĘ▒ÕĮōµŚČńÜäÕŖ¤ÕŖø’╝īń╗ØÕ»╣ÕåÖõĖŹÕć║Õ┐āõĖŁµā│Ķ”üńÜäõĖ£Ķź┐ŃĆéõ║ĵś»’╝īÕÅ¢ÕŠŚÕ░ŵÅÉńÉ┤ńĪĢÕŻ½ÕŁ”õĮŹÕÉÄ’╝īµłæÕģłÕÉĵŗ£õ║åÕ╝ĀÕĘ▒õ╗╗ŃĆüÕŹóńéÄŃĆüµ×ŚÕŻ░ń┐ĢõĖēõĮŹÕģłńö¤õĖ║ÕĖł’╝īÕŁ”ÕÆīÕŻ░ŃĆüÕŁ”Õ»╣õĮŹŃĆüÕŁ”ń╗ōµ×äŃĆüÕŁ”Õ”éõĮĢŌĆ£ńö©õĖĆń▓Æń¦ŹÕŁÉ’╝īń¦ŹÕć║õĖĆķóŚÕż¦µĀæŌĆØŃĆéĶ┐ÖõĖĆÕŁ”’╝īÕ░▒µĢ┤µĢ┤ÕŁ”õ║å8Õ╣┤ŃĆé ÕĮŁ’╝ÜĶ┐Ö8Õ╣┤µŚČķŚ┤’╝īµ£ēµ▓Īµ£ēÕüÜÕģČõ╗¢õ║ŗ’╝¤ ķĢŚ’╝ÜÕĮōńäȵ£ēŃĆéķÖżĶĄÜķÆ▒Õģ╗Õ«Čµ┤╗ÕÅŻÕż¢’╝īĶ┐śµ×äµĆØ8õĖ¬õ╣Éń½ĀńÜäµĀćķóśŃĆüõĖ╗ķóśŃĆüµø▓Õ╝ÅńŁēŃĆé ÕĮŁ’╝ÜÕÅŹÕć║ķüōĶ¦éŌĆöŌĆöÕēŹÕźÅµø▓’╝øÕÅżÕóōÕĖłÕŠÆŌĆöŌĆöÕźÅķĖŻµø▓Õ╝ÅńÜäÕ£åĶł×µø▓’╝øõŠĀõ╣ŗÕż¦ĶĆģŌĆöŌĆöÕÅśÕźÅµø▓’╝øķ╗»ńäČķöĆķŁéŌĆöŌĆöõĖēµ«ĄõĮōńÜäµé▓µŁī’╝øµĄĘµČøń╗āÕēæŌĆöŌĆöÕø×µŚŗµø▓’╝øµāģµś»õĮĢńē®ŌĆöŌĆöĶĄŗµĀ╝µø▓’╝øńŠżĶŗ▒Ķ┤║Õ»┐ŌĆöŌĆöÕżŹõĖēµ«ĄõĮōńÜäĶł×µø▓’╝ÜĶ░ĘÕ║ĢķćŹķĆóŌĆöŌĆöÕ╣╗µā│µø▓ŃĆéĶ┐Ö8õĖ¬õ╣Éń½Ā’╝īµČĄńø¢õ║åĶź┐µ¢╣ÕÅżÕģĖķ¤│õ╣ÉńÜäÕćĀõ╣ĵēƵ£ēµ£ĆķćŹĶ”üµø▓Õ╝Å’╝īÕģ©ķĢ┐60ÕżÜÕłåķƤŃĆéõĮĀÕåÖõ║åÕżÜõ╣ģ’╝¤ ķĢŚ’╝Üń£¤µŁŻÕŖ©ń¼öńÜ䵌ČķŚ┤ÕŬµ£ēÕŹŖÕ╣┤ŃĆéÕåÖÕ«īÕÉÄ’╝īµłæµŖŖµĆ╗Ķ░▒ÕÆīÕÅīķÆóńÉ┤ń╝®ÕåÖĶ░▒Õ»äń╗ÖõĖŁÕż«õ╣ÉÕøóÕłśÕźćĶĆüÕĖł’╝īÕ¦öµēśõ╗¢ÕĖ«Õ┐ÖÕ«ēµÄÆĶ»ĢÕźÅÕ╣Čõ┐«Ķ«óõĖĆõĖŗķģŹÕÖ©ŃĆéÕłśĶĆüÕĖłÕģłµ¢®ÕÉÄÕźÅ’╝īķćŹķģŹõ║åÕģČõĖŁÕģŁõĖ¬õ╣Éń½Ā’╝īÕ╣ČĶ»ĘķÖłõĮɵ╣¤Õģłńö¤µīćµīźõĖŁÕż«õ╣ÉÕøóĶ»ĢÕźÅŃĆéÕćŁĶ┐ÖõĖ¬Ķ»ĢÕźÅÕĖ”’╝īµłæń¤źķüōõ║åķŚ«ķóśµēĆÕ£©’╝īÕüÜõ║åõĖƵ¼ĪÕģ©µø▓Õż¦õ┐«µö╣ŃĆéÕÉÄµØź’╝īµłæķüćÕł░õ║åÕÅ”õĖĆõĮŹÕż¦ń¤źķ¤│Õ┤öńÄēńŻÉĶĆüÕĖłŃĆéÕ┤öĶĆüÕĖłÕÄåÕ░ĮĶē░ĶŠø’╝īõ║Ä1992Õ╣┤Õ║Ģ’╝īÕ£©ÕÅ░ÕīŚõĮ£õ║åŃĆŖńź×õ╣ÉŃĆŗńÜäõĖ¢ńĢīķ”¢µ╝öŃĆéõĖ║Ķ«®õĮ£Õōüµø┤Õ«īńŠÄ’╝īõ╗¢Ķ«®µłæĶć¬ÕĘ▒µīćµīźµÄÆń╗ā’╝īĶŠ╣µÄÆń╗āĶŠ╣õ┐«µö╣’╝īµĆÄõ╣łµö╣ķāĮõĖŹµ╗ĪµäÅńÜä’╝īõŠ┐µĢ┤µ«ĄķćŹÕåÖŃĆéµ▓Īµ£ēÕłśŃĆüÕ┤öõ║īõĮŹÕż¦ń¤źķ¤│’╝īÕ░▒µ▓Īµ£ēńÄ░Õ£©ńÜäŃĆŖńź×ķøĢõŠĀõŠŻõ║żÕōŹõ╣ÉŃĆŗŃĆéµēĆõ╗ź’╝īµŁŻÕ╝ÅÕć║ńēłµŚČ’╝īµłæńē╣Õł½Õ«ēµÄÆõ║åõĖĆķĪĄŌĆ£ķóśńī«Ķ»ŹŌĆØ’╝īµŖŖĶ┐Öķā©õĮ£Õōüķóśńī«ń╗Öõ╗¢õ╗¼ŃĆé ÕĮŁ’╝ÜŃĆŖńź×õ╣ÉŃĆŗµ»Åµ¼Īµ╝öÕć║’╝īķāĮÕŠŚÕł░õ╝ŚÕżÜĶĪīÕ«ČÕźĮĶ»äŃĆéÕÅ░µ╣ŠõĮ£µø▓Õ«ČķāŁĶŖØĶŗæÕģłńö¤Ķ»┤õĮĀńÜäŌĆ£õĮ£µø▓µŖƵ£»ķØ×ÕĖĖÕØÜÕ«×’╝īÕ╝”õ╣ÉÕÖ©ńÜäÕżäńÉåńē╣Õł½ÕźĮŌĆØŃĆéķ”ÖµĖ»Õ£Żõ╣ÉõĮ£µø▓Õ«ČµØ©õ╝»õ╝”Õģłńö¤Ķ»┤ŃĆŖńź×õ╣ÉŃĆŗŌĆ£õ╣āµłæµ¼ŻĶĄÅÕŹÄõ║║õĮ£Õōüõ║öÕŹüÕ╣┤µØźµēĆÕɼĶ┐ćµ£Ćń▓ŠÕĮ®ŃĆüµ£ĆÕæĢÕ┐āµ▓źĶĪĆõ╣ŗÕĘ©õĮ£ŌĆØŃĆ鵥ĘÕż¢õĮ£µø▓Õ«Čķ╗äÕ«ēõ╝”Ķ»┤ŌĆ£ķś┐ķĢŚńÜäķ¤│õ╣É’╝īÕ┐ģõ╝ÜÕ»╣µĢ┤õĖ¬õĖŁÕøĮõ╣ÉÕØøĶĄĘµĘ▒Õł╗ńÜäÕÉ»Ķ┐¬õĮ£ńö©ŌĆØŃĆéĶāĮÕÉ”Õģ¼Õ╝ĆõĮĀµłÉÕŖ¤ńÜäń¦śÕ»å’╝¤ ķĢŚ’╝ܵłÉÕŖ¤Ķ░łõĖŹõĖŖ’╝īÕ┐āÕŠŚÕĆƵ£ēõĖĆõ║øŃĆéŌĆ£µø▓õĖŹÕÄīµö╣ŌĆØ’╝īµ»Åµ╝öÕć║õĖƵ¼ĪµłæÕ░▒õ┐«µö╣õĖƵ¼Ī’╝īÕĮĢÕ«īķ¤│Ķ┐śµö╣õ║åõĖƵ¼ĪŃĆéÕż®õĖŗÕÄ©ÕĖł’╝īµŚĀõĖŹÕĖīµ£øÕł½õ║║Õ¢£µ¼óÕÉāõ╗¢ÕüÜÕć║µØźńÜäĶÅ£ŃĆéÕż®õĖŗõĮ£µø▓Õ«Č’╝īõ╣¤µŚĀõĖŹÕĖīµ£øÕł½õ║║Õ¢£µ¼óÕɼõ╗¢ÕåÖÕć║µØźńÜäķ¤│õ╣ÉŃĆéÕÄ©ÕĖłńÜäĶÅ£’╝īĶ”üĶē▓ŃĆüķ”ÖŃĆüÕæ│õ┐▒Õģ©’╝īµēŹõ╝ÜķŻ¤Õ«óÕ”éõ║æŃĆéõĮ£µø▓Õ«ČńÜäõĮ£Õōü’╝īõ╣¤Ķ”üÕźĮÕɼŃĆüĶĆÉÕɼ’╝īõ║║Õ«ČµēŹµä┐µäÅÕżÜÕɼŃĆéÕźĮÕɼ’╝īķ”¢ÕģłķØĀµŚŗÕŠŗŃĆéµēĆõ╗ź’╝īµłæĶŖ▒µ×üÕż¦ÕŖ¤Õż½ÕÄ╗ķöżńé╝ÕźĮÕɼĶĆīÕćåńĪ«ńÜ䵌ŗÕŠŗŃĆ鵳æńÜäÕ║¦ÕÅ│ķōŁõ╣ŗõĖƵś»ŌĆ£µŚŗÕŠŗõĖŹńŠÄµŁ╗õĖŹõ╝æŌĆØŃĆé ÕĮŁ’╝ÜõŠØµłæń£ŗ’╝īõĮĀÕĘ▓ĶŠŠÕł░õ║åĶć¬ÕĘ▒Ķ┐Įµ▒éńÜäÕłøõĮ£ÕóāńĢīŃĆéõĖŹõ╗ģŃĆŖńź×õ╣ÉŃĆŗ’╝īÕģČõ╗¢õĮ£Õōüõ╣¤ķāĮÕÉīµĀĘńÜäńŠÄĶĆīõĖŹńö£õ┐Ś’╝īķøģĶĆīõĖŹĶ┐éķģĖ’╝īÕ»īõĖĮõĖ░µ╗ĪĶĆīķĆŵśÄµŚĀÕ░śŃĆéÕÅ»µłæõĖŹÕż¬ńÉåĶ¦ŻõĮĀĶ»┤ńÜäŌĆ£µŚŗÕŠŗÕćåńĪ«ŌĆØ’╝īÕÅ»ÕÉ”Ķ¦ŻķćŖõĖĆõĖŗ’╝¤ ķĢŚ’╝ܵŚĀµĀćķóśńÜäń║»ķ¤│õ╣É’╝īõĖŹÕŁśÕ£©µŚŗÕŠŗÕćåńĪ«ńÜäķŚ«ķóśŃĆéµĀćķóśķ¤│õ╣É’╝īµł¢µś»Ķʤµ¢ćÕŁ”µ£ēÕģ│ńÜäķ¤│õ╣É’╝īÕłÖÕŁśÕ£©µś»ÕÉ”ÕćåńĪ«ńÜäķŚ«ķóśŃĆéµ»öµ¢╣Ķ»┤’╝īµØ©Ķ┐ćńÜäõĖ¬µĆ¦Õüŵ┐ĆŃĆüĶ▒¬µöŠ’╝īķāŁķØ¢ńÜäõĖ¬µĆ¦µĖ®ÕÄÜŃĆüÕåģµĢøŃĆéÕÉīµś»õĖƵØĪÕźĮÕɼµŚŗÕŠŗ’╝īķĆéÕÉłµØ©Ķ┐ćÕ░▒Ķé»Õ«ÜõĖŹķĆéÕÉłķāŁķØ¢ŃĆéÕÅŹõ╣ŗõ║”ńäČŃĆé ÕĮŁ’╝ÜĶĆÉÕɼńÜäÕģ│ķö«ńé╣ÕÅłÕ£©Õō¬ķćī’╝¤ ķĢŚ’╝ÜõĖƵś»ÕåģµČĄŃĆüµäÅÕóāĶ”üµĘ▒Õł╗ŃĆüµĘ▒ÕÄÜŃĆéõ║īµś»Õ»╣õĮŹ’╝łÕżŹĶ░ā’╝ēĶ”üõĖ░ÕÄÜŃĆéÕģČõĖŁÕÅłõ╗źÕ»╣õĮŹõĖ░ÕÄܵ£ĆķÜŠŃĆé ÕĮŁ’╝ÜķÜŠÕ£©Õō¬ķćī’╝¤ ķĢŚ’╝ܵłæńÜäõ║”ÕĖłõ║”ÕÅŗķ▓ŹÕģāµü║µĢֵijĶ»┤Ķ┐ć’╝ÜŌĆ£µ£ĆõĖŹķ£ĆĶ”üµĢÖńÜäĶ»Šµś»ķģŹÕÖ©’╝īµ£Ćķ£ĆĶ”üµĢÖńÜäĶ»Šµś»ÕżŹĶ░ā’╝łÕŹ│Õ»╣õĮŹ’╝ēŃĆéŌĆØõŠØµłæõĖ¬õ║║ń╗Åķ¬ī’╝īĶ┐×ÕÆīÕŻ░ŃĆüµø▓Õ╝ÅķāĮµ£ēÕÅ»ĶāĮĶć¬ÕŁ”ĶĆīµłÉŃĆéµā¤µ£ēÕ»╣õĮŹ’╝īµś»ķØ×Õ£©õĖźÕĖłµīćÕ»╝õ╣ŗõĖŗ’╝īĶŗ”ÕŁ”Ķŗ”ń╗ā’╝īõĖŹÕÅ»ĶāĮÕ╝äķĆÜŃĆéÕøĀõĖ║Õ«āÕż¬ÕżŹµØéŃĆüÕż¬Õø░ķÜŠŃĆéÕ░▒ÕźĮµ»öµŁ”ÕŖ¤õĖŁńÜäÕż¢ÕŖ¤õĖÄÕåģÕŖ¤ŃĆéÕż¢ÕŖ¤ÕÅ»Ķć¬ÕŁ”’╝īÕÅ»ŌĆ£ÕüĘÕĖłŌĆØŃĆéÕåģÕŖ¤ÕłÖķØ×ÕŠŚµśÄÕĖłÕ┐āõ╝ĀÕÅŻµÄł’╝īÕŖĀõĖŖÕŗżÕŁ”Ķŗ”ń╗āõĖŹÕÅ»ŃĆé ÕĮŁ’╝ÜõĮĀńö©õĖƵ«ĄÕ»╣Ķ░ł’╝īõĖƵ«Ąķ¤│õ╣ÉńÜäµ¢╣Õ╝Å’╝īµŗŹµłÉDVD’╝īõĮ£õĖ║ŃĆŖńź×õ╣ÉŃĆŗCDńÜäķÖäĶĄĀÕōüŃĆéĶ┐ÖÕ»╣õĖŹń夵éēõ║żÕōŹõ╣ÉńÜäõ║║’╝īµś»ÕŠłÕźĮńÜäÕ»╝ÕɼµĢÖµØÉŃĆéÕźĮÕāÅõ╗ĵ£¬Ķ¦üĶ┐ćĶ┐ÖµĀĘńÜäÕüܵ│ĢŃĆéõĮĀµś»µĆÄõ╣łµā│Õł░Ķ┐ÖõĖ¬µ¢╣µ│ĢńÜä’╝¤µłæµøŠÕŽµłæńÜäÕ░ÅÕÉīõ║ŗÕ╝ĀÕŹōõĖĆĶĄĘµØźĶ¦éń£ŗõĮĀńÜäDVD’╝īÕĮōń£ŗÕł░Õ»╣Ķ░ł’╝īõ╗¢ĶĘ│ĶĄĘµØźĶ»┤’╝ÜŌĆ£ÕōÄÕæĆ’╝īµłæõĖŖĶ»ŠńÜ䵌ČÕĆÖķāĮÕÅ»õ╗źńö©Ķ┐Öµ«Ą’╝üŌĆØĶ»ĘķŚ«õĮĀõ╗ŗõĖŹõ╗ŗµäŵłæÕƤń╗Öõ╗¢õĖŖĶ»Šńö©õĖĆõĖŗ’╝īÕĮōńäČÕ┐ģķĪ╗ÕĮōµŚźÕƤÕĮōµŚźĶ┐śńÜäŃĆé ķĢŚ’╝ÜÕĮōµ£łÕƤÕĮōµ£łĶ┐śõ╣¤µ▓ĪķŚ«ķóś’╝īÕŬĶ”üõĮĀµöŠÕŠŚõĖŗÕ┐āŃĆé’╝łõĖĆń¼æ’╝ēµø┤õĮĢÕåĄµ£ēõ║║µ¼ŻĶĄÅ’╝īķ鯵ś»µ▒éķāĮµ▒éõĖŹµØźńÜäńŠÄõ║ŗÕæó’╝üõĮ£µø▓ĶĆģÕåÖÕ«īõĮ£Õōü’╝īõ╗ģõ╗ģµś»Õ«īµłÉń¼¼õĖĆÕ║”ÕłøõĮ£ŃĆéÕö▒ÕźÅÕ«ČńÜäµ╝öÕö▒µ╝öÕźÅ’╝īµś»ń¼¼õ║īÕ║”ÕłøõĮ£ŃĆéÕģČķćŹĶ”üµĆ¦õĖĆńé╣õĖŹµ»öń¼¼õĖĆÕ║”ÕłøõĮ£õĮÄ’╝īÕ«āÕĖĖÕĖĖÕå│Õ«Üõ║åń¼¼õĖĆÕ║”ÕłøõĮ£ńÜäŌĆ£ńö¤µŁ╗ŌĆØŃĆéĶ┐śµ£ēń¼¼õĖēÕ║”ÕłøõĮ£’╝īÕ░▒µś»µ¼ŻĶĄÅŃĆéĶ»ŚŃĆüńö╗ńÜäµ¼ŻĶĄÅ’╝īµ¼ŻĶĄÅĶĆģńø┤µÄźķØóÕ»╣ńÜ䵜»ÕĤõĮ£ŃĆéÕÅ»µś»ķ¤│õ╣ɵ¼ŻĶĄÅ’╝īµ¼ŻĶĄÅĶĆģķØóÕ»╣ńÜ䵜»õ║īÕ║”ÕłøõĮ£’╝īÕŹ│µ╝öÕö▒µ╝öÕźÅŃĆéÕ”éõĮĢµÉŁõĖĆÕ║¦µĪź’╝īµ▓¤ķĆÜõĖēĶĆģ’╝īµś»µłæµĆØĶĆāõ║åÕżÜÕ╣┤ńÜäĶ»ŠķóśŃĆéÕłÜÕźĮ’╝īŃĆŖńź×õ╣ÉŃĆŗńÜäÕĮĢķ¤│ÕÉłń║”ńŁŠĶ«óÕÉÄ’╝īµīćµīźķ║”Õ«Čõ╣ÉÕģłńö¤Õ╗║Ķ««µłæÕżÜÕ╝ĆõĖĆÕ£║ķ¤│õ╣Éõ╝Ü’╝īÕ╣ČÕģ©ń©ŗÕĮĢÕāÅŃĆ鵳æĶ«Īń«ŚõĖĆõĖŗĶ┤╣ńö©’╝īÕ░ÜĶ┤¤µŗģÕŠŚĶĄĘ’╝īõŠ┐ńŁöÕ║öõ║åŃĆéÕÅ»µś»ÕĮĢÕ«īÕÉÄõĖĆń£ŗ’╝īµŗŹõĖŹÕģ©’╝īµŚĀµ│ĢµĢ┤ÕØŚõĮ┐ńö©ŃĆéÕø×Õł░ÕÅ░µ╣ŠÕÉÄ’╝īõŠ┐ÕŖĀµŗŹõ║åÕ»╣Ķ»Ø’╝īÕē¬ĶŠæµłÉńÄ░Õ£©ńÜäµĀĘÕŁÉŃĆéķ鯵ś»µŚĀÕ┐āµÅƵ¤│’╝īń╗ōµ×£ÕŹ┤µ¤│µÜŚĶŖ▒µśÄŃĆéń£¤Ķ”üĶ░óÕż®Ķ░óÕ£░Ķ░óõ║║’╝ü ÕĮŁ’╝ÜÕæĄÕæĄ’╝īń£¤µś»õ║║ń«ŚõĖŹÕ”éÕż®µäÅ’╝īõĖ║õĮĀķ½śÕģ┤ŃĆéÕ£©CDńÜäÕåīķĪĄõĖŖ’╝īń£ŗÕł░õĮĀĶʤķćæÕ║ĖńÜäÕÉłńģ¦õ╗źÕÅŖõ╗¢ķĆüń╗ÖõĮĀńÜäķóśÕŁŚŃĆéõĮĀµś»µĆĵĀĘĶʤķćæÕż¦õŠĀµłÉõĖ║µ£ŗÕÅŗńÜä’╝¤ ķĢŚ’╝ܵ£ŗÕÅŗĶ░łõĖŹõĖŖ’╝īµłæÕŬµś»õ╗¢ńÜäÕ┐ĀÕ«×Ķ»╗ĶĆģÕÆīÕ┤ćµŗ£ĶĆģ’╝īõ╣¤µś»ÕŠŚńøŖĶĆģŃĆé ÕĮŁ’╝ܵĆÄõ╣łĶ»┤’╝¤ ķĢŚ’╝ÜÕŬĶ░łõĖĆńé╣ķćæÕ║ĖµŁ”õŠĀÕ░ÅĶ»┤Õ»╣µłæķ¤│õ╣ÉÕłøõĮ£ńÜäķćŹÕż¦ÕÉ»ńż║ÕɦŃĆ鵳æĶ¦ēÕŠŚķćæÕ║ĖÕ░ÅĶ»┤ńÜäµ£ĆµłÉÕŖ¤Õżä’╝īµś»Õż¢õ┐ŚÕåģķøģŃĆéÕż¢õ┐Ś’╝īĶ«®Õ«āµŗźµ£ēõ╝ŚÕżÜĶ»╗ĶĆģŃĆéÕåģķøģ’╝īĶ«®Õ«āń╗ÅÕŠŚĶĄĘÕÅŹÕżŹĶĄÅĶ»╗ŃĆ鵳æõĖĆńø┤Ķ┐Įµ▒éĶć¬ÕĘ▒ńÜäõĮ£Õōüõ╣¤Õģʵ£ēŌĆ£Õż¢õ┐ŚÕåģķøģŌĆØńÜäńē╣Ķ┤©ŃĆé ÕĮŁ’╝ÜõĮĀµŗłÕć║ŌĆ£Õż¢õ┐ŚÕåģķøģŌĆØÕøøõĖ¬ÕŁŚ’╝īõ╗żµłæÕ┐ĮńäČĶüöµā│Õł░’╝īĶ┐Öµś»õĖĆõĖ¬ÕŠłÕźĮńÜäĶ«║µ¢ćķóśńø«ŃĆéµ»öµ¢╣Ķ»┤’╝īŃĆŖĶ«║ķćæÕ║ĖÕ░ÅĶ»┤ńÜäÕż¢õ┐ŚÕåģķøģŃĆŗ’╝īµł¢µś»ŃĆŖĶ«║ķś┐ķĢŚõĮ£ÕōüńÜäÕż¢õ┐ŚÕåģķøģŃĆŗŃĆé ķĢŚ’╝ÜĶ░óĶ░óµŖ¼õĖŠ’╝üµłæĶ¦ēÕŠŚµłæńÜäõĮ£ÕōüŌĆ£Õż¢õ┐ŚŌĆØ’╝īõĖ╗Ķ”üĶĪ©ńÄ░Õ£©µ»ÅõĖƵø▓ńÜ䵌ŗÕŠŗŃĆüķ¤│Ķ░ā’╝īÕ░▒ÕāÅõĖĆĶł¼õĖŁÕøĮõ║║µēĆÕ¢£ńł▒Ķ»ĄĶ»╗ńÜäÕÅżĶ»ŚĶ»ŹõĖƵĀĘ’╝īńÉģńÉģõĖŖÕÅŻ’╝īõ╝╝µøŠńøĖĶ»åÕŹ┤ÕÅłÕ╣ČõĖŹń£¤ńÜäĶ«żĶ»åŃĆéŌĆ£ÕåģķøģŌĆØ’╝īÕłÖõĖ╗Ķ”üĶĪ©ńÄ░Õ£©õĖżµ¢╣ķØóŃĆéõĖƵś»µ£ēŌĆ£ķ¤│Õż¢õ╣ŗµäÅŌĆØ’╝īõ║īµś»µ£ēń╗ÅÕŠŚĶĄĘÕÅŹÕżŹµÄ©µĢ▓ŃĆüÕżÜÕɼÕćĀµ¼ĪńÜäÕ»╣õĮŹŃĆé ÕĮŁ’╝ÜķćæÕ║ĖÕ░ÅĶ»┤Õ»╣õĮĀĶ┐śµ£ēÕō¬õ║øķćŹĶ”üÕĮ▒ÕōŹ’╝¤ ķĢŚ’╝ÜÕ░ÅĶ»┤õĖŁÕŠłÕżÜõ║║ńē®ÕŁ”µŁ”ŃĆüń╗āµŁ”ŃĆüµłÉµØÉńÜäĶ┐ćń©ŗ’╝īÕ»╣µłæÕŁ”ńÉ┤ŃĆüń╗āńÉ┤ŃĆüµĢÖńÉ┤’╝īõ╣¤ńöܵ£ēÕÉ»ńż║ŃĆéõŠŗÕ”é’╝īµłæµøŠĶć¬Õłøõ║åõĖĆÕźŚŌĆ£Õ░ŵÅÉńÉ┤Õ¤║µ£¼ÕŖ¤Õż½ÕŹüÕģ½µŗøŌĆØ’╝īÕ░▒µś»ÕÅŚõ║åŃĆŖÕ░äķøĢĶŗ▒ķøäõ╝ĀŃĆŗõĖĆõ╣”õĖŁµ┤¬õĖāÕģ¼ŌĆ£ķÖŹķŠÖÕŹüÕģ½µÄīŌĆØńÜäÕĮ▒ÕōŹŃĆéĶ┐æÕ╣┤µØź’╝īµłæĶć¬Õłøõ║åõĖĆÕźŚŌĆ£ķ╗äķƤÕ░ŵÅÉńÉ┤µĢÖÕŁ”µ│ĢŌĆØ’╝īµŖŖÕ░ŵÅÉńÉ┤ÕÅśÕŠŚµ»öĶŠāµśōµĢÖŃĆüµśōÕŁ”’╝īĶ┐×µłÉÕ╣┤õ║║õ╣¤ÕÅ»õ╗źÕŠłĶĮ╗µØŠÕ£░µŗēÕć║ÕźĮÕɼńÜäÕŻ░ķ¤│ŃĆéĶ┐Įµ║»ń╝śńö▒’╝īńÜåÕøĀĶć¬ÕĘ▒ķØ×Ķ”üÕłøÕć║õĖĆÕźŚµŁ”ÕŖ¤µØźõĖŹÕÅ»’╝īµēŹĶ¦ēÕŠŚĶ┐ćńśŠ’╝īÕźĮńÄ®ŃĆéÕ£©ŃĆŖĶĄÅõ╣ɵØéĶ░łŃĆŗõĖƵ¢ćõĖŁ’╝īµłæµŖŖĶź┐µ¢╣Ķ»ĖÕż¦ÕĖłńÜäń«ĪÕ╝”õ╣ÉķģŹÕÖ©µēŗµ│Ģ’╝īµĢ┤ńÉåÕæĮÕÉŹõĖ║ŌĆ£ńŠżķøäÕŖ®Õ©üŌĆØŃĆüŌĆ£ÕŹāÕåøõĖćķ®¼ŌĆØŃĆüŌĆ£ķĢ┐õĖŁµ£ēń¤ŁŌĆØńŁēń▒╗õ╝╝õĖŁÕøĮÕŖ¤Õż½ńÜäÕÉŹń¦░ŃĆéĶ┐ÖÕż¦µ£ēÕŖ®õ║ĵłæĶć¬ÕĘ▒Ķ«░õĮÅŃĆüńÉåĶ¦ŻŃĆüõĮ┐ńö©Õ«āõ╗¼ŃĆé ÕĮŁ’╝ÜõĮĀµøŠõĖ║õĖŁÕøĮÕÅżĶ»ŚĶ»ŹÕÆīõĖŁÕøĮń╗ÅÕģĖµĀ╝Ķ©ĆĶ░▒Ķ┐ćÕŠłÕżÜµø▓’╝īÕåÖĶ┐ćÕøøÕ╣ĢµŁīÕē¦ŃĆŖĶź┐µ¢ĮŃĆŗ’╝īÕåÖĶ┐ćń▓żĶ»ŁĶē║µ£»µŁīµø▓’╝īÕåÖĶ┐ćÕż¦ķćÅõ╣ÉĶ»äŃĆüõ╣ÉĶ«║ŃĆéń£ŗµØź’╝īõĮĀÕ»╣µ¢ćÕŁ”ńÜäÕ¢£ńł▒’╝īõ╝╝õ╣ÄõĖŹõĖŗõ║Äķ¤│õ╣ÉŃĆéĶ║½õĖ║ŌĆ£ÕÖ©õ╣Éõ║║ŌĆØ’╝īõĮĀńÜäµ¢ćÕŁ”Õģ┤ĶČŻµś»µĆÄõ╣łÕ¤╣Õģ╗Õć║µØźńÜä’╝¤ ķĢŚ’╝ÜÕø×µā│ĶĄĘµØź’╝īµłæńÜäķ¤│õ╣ÉÕÉ»ĶÆÖõĖĵ¢ćÕŁ”ÕÉ»ĶÆÖ’╝īÕćĀõ╣ĵś»ÕÉīµŚČŃĆéÕ╣╝Õ╣┤Õ£©Õ╣┐õĖ£õ╣ĪõĖŗ’╝īÕĖĖÕɼµ»Źõ║▓Õö▒µ£©ķ▒╝õ╣”’╝īÕÉ¼Õż¦õ║║Õö▒ń▓żµø▓’╝īķ鯵ś»ķ¤│õ╣ÉÕÉ»ĶÆÖŃĆéĶ┐śµ£¬õĖŖÕ░ÅÕŁ”’╝īµ»öµłæķĢ┐10Õ▓üńÜäõ║īÕōź’╝īÕ╝║ķĆ╝µłæµ»ÅÕż®µŖäõ╣”õĖĆń»ć’╝īµŖäõĖŹÕć║µØźÕ░▒ńĮܵēōµēŗµÄīŃĆéķ鯵ś»µ¢ćÕŁ”ÕÉ»ĶÆÖŃĆéÕł░Õ░ÅÕŁ”õĖēÕ╣┤ń║¦ÕÉÄ’╝īõ║īÕōźńÜäõĖĆÕż¦ÕĀåÕ░ÅĶ»┤ńŁē’╝īÕ░▒µłÉõ║åµłæµ»ÅÕż®ńÜäń▓Šńź×ĶÉźÕģ╗ÕōüŃĆéõĖŖõ║åÕ╣┐ÕĘ×ķ¤│õĖōķÖäõĖŁ’╝īµ£Ćńö©ÕŖ¤ńÜäÕÉīÕŁ”µĢ┤Õż®ķÆ╗ńÉ┤µł┐’╝īµłæÕŹ┤ÕĖĖÕĖĖķÆ╗ÕøŠõ╣”ķ”å’╝īõ║½ÕÅŚĶ»╗õĖ¢ńĢīÕÉŹĶæŚŃĆüÕɼõĖ¢ńĢīÕÉŹµø▓õ╣ŗõ╣ÉŃĆéµ▓Īµ£ēÕł╗µäÅÕÄ╗Õ¤╣Õģ╗’╝īõĖĆÕłćńÜåÕć║õ║ÄĶć¬ńäČ ÕĮŁ’╝ܵ¢ćÕŁ”Õ»╣õĮĀńÜäķ¤│õ╣ÉÕłøõĮ£’╝īµ£ēÕō¬õ║øķćŹÕż¦ÕĮ▒ÕōŹ’╝¤ ķĢŚ’╝ÜÕż¦ÕōēµŁżķŚ«’╝üķ”¢Õģł’╝īµś»ÕĮ▒ÕōŹÕł░ķóśµØÉńÜäķĆēµŗ®ŃĆéµłæµ»öĶŠāÕż¦ńÜäÕćĀķā©ÕÖ©õ╣ÉõĮ£Õōü’╝īÕīģµŗ¼ŃĆŖńź×ķøĢõŠĀõŠŻõ║żÕōŹõ╣ÉŃĆŗŃĆüŃĆŖĶɦÕ│░õ║żÕōŹĶ»ŚŃĆŗŃĆüµ░æõ╣ÉÕÉłÕźÅŃĆŖń¼æÕé▓µ▒¤µ╣¢ŃĆŗ’╝īÕģ©µś»ÕøĀĶ»╗ķćæÕ║ĖµŁ”õŠĀÕ░ÅĶ»┤ĶĆīĶÉīÕÅæÕć║ÕłøõĮ£ńüĄµä¤ŃĆéÕ░ŵÅÉńÉ┤ÕŹÅÕźÅµø▓ŃĆŖń¦ŗńæŠŃĆŗŃĆüÕ░ŵÅÉńÉ┤õĖÄÕ╝”õ╣Éķś¤ŃĆŖĶź┐µ¢ĮÕ╣╗µā│µø▓ŃĆŗ’╝īÕ╝”õ╣ÉÕÉłÕźÅŃĆŖķÖłõĖ╗ń©ÄõĖ╗ķóśÕÅśÕźÅµø▓ŃĆŗńŁē’╝īķāĮµś»õ╗źõ╣ÉÕåÖõ║║ŃĆéÕåÖõ║║’╝īÕ┐ģńäČń”╗õĖŹÕ╝Ƶ¢ćÕŁ”µĆ¦ńÜäµĆØń╗┤µ¢╣Õ╝ÅŃĆéÕ░åÕģĘĶ▒ĪńÜäµ¢ćÕŁ”ÕåģµČĄõĖĵŖĮĶ▒ĪńÜäķ¤│õ╣ÉĶ»ŁĶ©ĆĶ׏õĖ║õĖĆõĮō’╝īĶ┐ÖµŁŻµś»µłæĶ┐ĮÕ»╗ŌĆ£Õż¢õ┐ŚÕåģķøģŌĆØńÜäµŗøµĢ░õ╣ŗõĖĆŃĆéÕģȵ¼Ī’╝īµś»ńø┤µÄźõĖ║ÕÅżõ╗ŖĶ»ŚĶ»ŹĶ░▒µø▓ŃĆéĶ┐śµ£ēķā©ÕłåõĮ£Õōü’╝īµłæńø┤µÄźÕÅéõĖÄõ║åµ¢ćÕŁ”ÕłøõĮ£ŃĆé ÕĮŁ’╝ÜõĮĀÕŬĶ░łÕł░Õ▒×õ║ÄÕż¢Õ£©ńÜäŃĆüĶĪ©Õ▒éńÜäŃĆüµśŠµĆ¦ńÜäÕĮ▒ÕōŹŃĆéÕåģÕ£©ńÜäŃĆüµĘ▒Õ▒éńÜäŃĆüķÜɵƦńÜäÕĮ▒ÕōŹÕæó’╝¤µłæõĖŹõ╗ģµ│©µäÅÕł░õĮĀõĖ║ÕÅżõ╗ŖĶ»ŚĶ»ŹĶ░▒µø▓ĶČģĶ┐ćõ║å100ķ”¢’╝īĶ┐śÕÅæńÄ░’╝īõĮĀńÜäõĖĆķā©ŃĆŖķś┐ķĢŚõ╣ÉĶ«║ŃĆŗ’╝īÕģĖķøģÕĘźÕʦ’╝īõ╝Ėń╝®Ķć¬Õ”é’╝īĶ┐ÖķÜŠķüōõĖŹµś»õĖŁÕøĮÕÅżÕģĖµ¢ćÕŁ”ń╗ÖõĮĀÕł╗õĖŗńÜäńāÖÕŹ░’╝¤õĮĀµł¢Ķ«Ėµ▓Īµ£ēńĢÖµäÅÕł░’╝īµ¢ćÕŁ”Õ«ØÕ║ōõĖŁķéŻõ║øÕÄåń╗ÅÕŹāńÖŠÕ╣┤µĘśµ┤ŚĶĆīķŁģÕŖøķÜĮµ░ĖńÜäńŠÄµ¢ćŃĆüńŠÄĶ»Ś’╝īÕĘ▓ń╗ŵĖŚķĆÅÕł░õĮĀķ¬©ÕŁÉķćī’╝īĶ׏Õī¢Õ£©õĮĀĶĪƵČ▓õĖŁõ║åŃĆéõ╗╗õĮĢĶē║µ£»ÕĮóÕ╝ÅķāĮĶ┐Įµ▒éńŠÄ’╝īķ¤│õ╣ÉĶē║µ£»ńÜäÕĮóÕ╝ŵ▓Īµ£ēńÉåńö▒õĖŹĶ┐Įµ▒éńŠÄŃĆéńŠÄ’╝īĶ┐ÖµŁŻµś»ÕÅżõ╗ŖõĖŁÕż¢Ķē║µ£»Õż¦ÕĖłõ╗¼ÕæĢÕ┐āµ▓źĶĪĆĶĆīõ╣ɵŁżõĖŹń¢▓õ╣ŗµĀ╣µ£¼ÕŖ©ÕŖø’╝īõ╣¤µŁŻµś»ń╗ÅÕģĖõĮ£ÕōüĶāĮĶČģĶČŖµŚČõ╗ŻŃĆüµ░æµŚÅõĖÄķśČń║¦’╝īķ£ćµÆ╝µŚĀµĢ░õ║║Õ┐āõ╣ŗµĀ╣µ£¼ÕĤÕøĀŃĆéµēĆõ╗źµłæµā│µø┤Ķ┐øõĖƵŁźÕ£░Ķ»┤’╝īµŁŻµś»ÕøĀõĖ║õĮĀÕ»╣ķ¤│õ╣ÉõĖĵ¢ćÕŁ”µ£ēÕÉīńŁēń©ŗÕ║”ńÜäÕ¢£ńł▒õ╗źÕÅŖÕÉīµĀĘõĖ░ÕÄÜńÜäń¦»ń┤»’╝īµēŹµ╗ŗÕģ╗Õć║õĮĀÕ»╣ńŠÄńÜäÕ╝éÕĖĖµĢŵ䤒╝īµ┐ĆÕÅæÕć║õĮĀÕ»╣ńŠÄńÜäµē¦ńØĆĶ┐ĮÕ»╗’╝īķö╗ķĆĀÕć║õĮĀĶĪ©ńÄ░ńŠÄńÜäńŗ¼ńē╣ÕåģÕŖ¤ŃĆéõ║ĵś»’╝īķ¤│ńŖ╣µ£¬Õ░ĮµŚČõĮĀõ╗źõ╣ÉÕ┐āÕģźµ¢ć’╝īĶ©ĆńŖ╣µ£¬Õ░ĮµŚČõĮĀõ╗źµ¢ćÕ┐āÕģźõ╣É’╝īÕÅłńö▒µŁżĶĆīĶĮ«Õø×ÕŠĆÕżŹÕ£░ŌĆ£µČģµ¦āŌĆØķćŹńö¤ŃĆéÕż¢õ║║ń£ŗĶĄĘµØźõĮĀÕ£©ķ¤│õ╣ÉÕÆīµ¢ćÕŁ”µ«┐ÕĀéõ╣ŗķŚ┤µĖĖĶĄ░Õ”éķŠÖ’╝īµś»Õ”éõĮĢńÜäµĮćµ┤ÆńŚøÕ┐½’╝īÕÅ»µ£ēĶ░üń¤ź’╝īÕåģõĖŁńÜäŌĆ£ķÖŹķŠÖÕŹüÕģ½µÄīŌĆØ’╝īÕ▓鵜»õĖƵ£ØõĖĆÕżĢÕŠŚµØźõ╣ŗÕŖ¤’╝üµłæµā│’╝īÕŬµ£ēĶ┐Öõ╣łĶ»┤’╝īµēŹń£¤µŁŻĶ»┤ÕŠŚµĖģµźÜ’╝ܵ£ēńØĆÕ╣┐õĖ£Õ壵░æĶĪĆĶäēńÜäńŠÄń▒ŹÕÅ░µ╣ŠõĮ£µø▓Õ«Čķś┐ķĢŚ’╝īõĮĢõ╗źµ£ēÕ”éµŁżÕ┐ŚĶČŻõĖÄÕŖ¤ÕŖø’╝īµåŗĶČ│28Õ╣┤õ╣ŗń£¤µ░ö’╝īõĖ║õ║żÕōŹõ╣ÉĶ┐ÖõĖĆĶź┐µ¢╣ÕÅżÕģĖķ¤│õ╣ÉĶéīõĮōµ│©ÕģźÕĮōõ╗ŻÕŹÄÕżÅµ¢ćÕŁ”ńÜäĶĪƵČ▓’╝īõĮ┐ÕģČķ¤│õ╣Éńö¤ÕæĮķÖĪńäČķŚ┤µ┤╗µ│╝µ│╝ńāŁĶŠŻĶŠŻĶĄĘµØźŃĆéÕÉīµäŵłæĶ┐ÖµĀĘĶ»┤ÕÉŚ’╝¤ ķĢŚ’╝Üõ╗ĵ£¬µ£ēõ║║Ķ┐ÖµĀĘÕŁÉµØźµŖĮÕÅ¢µłæńÜäĶĪƵČ▓ÕÆīķ¬©ķ½ōĶ┐øĶĪīÕī¢ķ¬īŃĆ鵳æõĖŹń¤źĶ»┤õ╗Ćõ╣łÕźĮ’╝īń£ŗµØźÕÅ¬ÕźĮÕƤńö©õĮĀńÜäĶ»Øõ║å’╝ÜŌĆ£µä¤Ķ¦ēõ║öĶäÅÕģŁĶģæõ╣āĶć│Õģ©Ķ║½µ»ÅõĖ¬ń╗åĶā×ķāĮÕ╝ĀÕ╝ĆµØźµĘ▒Õæ╝ÕÉĖŃĆéŌĆØ ÕĮŁ’╝ÜÕ”éµ×£Ķ”üķĆēÕć║ÕćĀķā©õ╗ŻĶĪ©õĮ£’╝īõĮĀõ╝ÜķĆēÕō¬ÕćĀķā©’╝¤ ķĢŚ’╝ÜĶ┐ÖõĖ¬ķŚ«ķóś’╝īÕ░▒ÕāÅķŚ«õĖĆõĮŹÕ”łÕ”ł’╝ÜõĮĀµ£ĆÕ¢£µ¼óõĮĀĶć¬ÕĘ▒ńÜäÕō¬õĖĆõĖ¬ÕŁ®ÕŁÉ’╝¤µłæńøĖõ┐ĪÕż¦ÕżÜµĢ░Õ”łÕ”łķāĮÕŠłķÜŠõĮ£ńŁöŃĆéÕ”éµ×£õĖŹĶāĮõĖŹķĆē’╝īµłæÕż¦µ”éõ╝ÜķĆē’╝Üń¼¼õĖĆ’╝īŃĆŖńź×ķøĢõŠĀõŠŻõ║żÕōŹõ╣ÉŃĆŗŃĆéń¼¼õ║ī’╝īµŁīÕē¦ŃĆŖĶź┐µ¢ĮŃĆŗŃĆéń¼¼õĖē’╝īÕÉłÕö▒ŃĆŖÕ▓üջƒ╝īńäČÕÉÄń¤źµØŠµ¤Åõ╣ŗÕÉÄÕćŗŃĆŗŃĆéń¼¼Õøø’╝īÕÅżĶ»ŚĶ»Źńŗ¼Õö▒ŃĆŖķö”ńæ¤ŃĆŗŃĆé ÕĮŁ’╝ܵ£ĆÕÉÄ’╝īķŚ«õĮĀõĖĆõĖ¬õ╣¤Ķ«Ėµ£ēńé╣µĢŵä¤ńÜäķŚ«ķóś’╝ÜõĮĀÕ»╣Ķ░ŁńøŠńÜäõĮ£ÕōüµĆÄõ╣łń£ŗ’╝¤ ķĢŚ’╝Ü1988Õ╣┤’╝īµłæÕ£©ķ”ÖµĖ»ŃĆŖµśÄµŖźµ£łÕłŖŃĆŗÕÅæĶĪ©Ķ┐ćŃĆŖĶ«┐Ķ░ŁńøŠŃĆŗõĖƵ¢ć’╝īÕ»╣õ╗¢ÕżÜµ¢╣µÄ©Õ┤ć’╝īÕ╣ČÕ»äõ╗źÕÄܵ£øŃĆéµøŠĶ«░ÕŠŚÕÅČĶü¬ÕÉæµłæµÄ©ĶŹÉĶ░ŁńøŠńÜäµ»ĢõĖÜõĮ£ÕōüŃĆŖńü½ŃĆŗ’╝łÕģ©ÕÉŹĶ«░õĖŹÕŠŚõ║å’╝ē’╝īµłæõ╗źõĖ║ķ鯵ś»Ķć│õ╗ŖõĖ║µŁóµłæÕɼĶ┐ćõ╗¢µ£ĆÕźĮńÜäõĮ£ÕōüŃĆéĶ┐Öõ║øÕ╣┤µØź’╝īõ╗¢ń║óķĆÅÕģ©õĖ¢ńĢīŃĆ鵳æõĖ║õ╗¢ķ½śÕģ┤õ╣ŗõĮÖ’╝īõ╣¤µ£ēõĖĆńé╣µØ×õ║║Õ┐¦Õż®’╝ÜÕ”éµ×£µ▓Īµ£ēõĖĆõ║øÕźĮÕɼŃĆüĶĆÉÕɼńÜäõĮ£ÕōüńĢÖõĖŗµØź’╝īÕŹ│õĮ┐Õģ©õĖ¢ńĢīµēƵ£ēÕź¢µØ»ķāĮÕ£©µēŗõĖŖ’╝īõĖĆńÖŠÕ╣┤ÕÉÄ’╝īķŻÄÕģēĶ┐śõ╝ÜÕ£©ÕÉŚ’╝¤ÕÅżõ║║Ķ»┤’╝īŌĆ£ÕÅæĶ┤óń½ŗÕōüŌĆØŃĆéÕ”éµŖŖõĮ£µø▓Õ«ČńÜäŌĆ£ÕÉŹŌĆص»öÕ¢╗õĖ║ŌĆ£Ķ┤óŌĆØ’╝īÕźĮÕɼĶĆÉÕɼńÜäõĮ£Õōüµ»öÕ¢╗õĖ║ŌĆ£ÕōüŌĆØ’╝īĶ░ŁńøŠÕģäõ╣¤Ķ«ĖÕł░õ║åÕżÜĶ┐Įµ▒éŌĆ£ÕōüŌĆØ’╝īÕ░æĶ┐Įµ▒éŌĆ£Ķ┤óŌĆØńÜ䵌ČÕĆÖõ║åŃĆéõ╗ÄķĢ┐Ķ┐£ń£ŗ’╝īõĮ£µø▓Õ«ČńÜäõĖōõĖÜÕ£░õĮŹŃĆüÕÄåÕÅ▓Õ£░õĮŹ’╝īÕŬĶāĮķØĀõĮ£ÕōüÕźĮÕɼŃĆüĶĆÉÕɼ’╝īõ║”ÕŹ│õĮĀÕłÜµēŹµēĆÕ╝║Ķ░āńÜäŌĆ£ńŠÄŌĆØ’╝īµØźÕ╗║ń½ŗŃĆéĶłŹµŁżńÜåķØ×µŁŻķĆöŃĆé ÕĮŁ’╝ܵ£ēµ▓Īµ£ēõĖĆń¦ŹÕÅ»ĶāĮ’╝īÕüćĶŗźĶĄ░Ķ┐øÕÅ”õĖĆõĖ¬Ķ»ØĶ»ŁÕ£łÕŁÉ’╝īÕ£©ÕĮ╝Õ£łÕ£łÕåģõ║║ń£ŗµØź’╝īõ║║Õ«ČµēĆÕŁ£ÕŁ£Ķ┐Įµ▒éńÜ䵣Żµś»õĮĀµēĆĶ»┤ńÜäŌĆ£ÕōüŌĆØ’╝¤ ķĢŚ’╝Üń╗ŵĄÄŃĆüµö┐µ▓╗ŃĆüń¦æµŖĆķāĮÕż®Õż®Õ£©ÕÅś’╝īńöÜĶć│ķüōÕŠĘÕćåÕłÖõ╣¤Õ£©ÕÅśŃĆéõĮåõ║║µĆ¦ŃĆüõ║║µāģÕŹ┤ÕŹāÕ╣┤õĖŹÕÅś’╝īõ║║ńÜäń£╝ŃĆüĶĆ│ŃĆüķ╝╗ŃĆüĶłīõ╣ŗÕ¤║µ£¼ķ£Ćµ▒é’╝īõ╣¤ÕŹāõĖćÕ╣┤õĖŹÕÅśŃĆ鵳æõ┐Īõ╗╗ÕÄåÕÅ▓’╝īµēĆõ╗źõ╣Éõ║ĵŖŖĶ┐ÖõĖ¬õ║ēĶ«║’╝īõ║żń╗ÖÕÄåÕÅ▓ÕÄ╗õĮ£ĶŻüÕå│ŃĆé ÕĮŁ’╝Üõ╗Ćõ╣łµŚČÕĆÖõĮĀĶ”üµś»Õø×Õ╣┐ÕĘ×µÄóõ║▓’╝īÕĖīµ£øĶāĮÕł░µ»ŹµĀĪÕ╝ĆÕ╝ĆĶ«▓Õ║¦ŃĆ鵳æÕŠłÕĖīµ£øÕŁ”ńö¤õ╗¼ń¤źķüō’╝ÜÕÅ░µ╣Šµ£ēõĖ¬õ╗ÄÕÆ▒õ╗¼µś¤µĄĘķ¤│õ╣ÉÕŁ”ķÖóÕć║ÕÄ╗ńÜä’╝īÕģģµ╗ĪńØ┐µÖ║ńÜäŃĆüńüĄÕģēÕøøÕ░äńÜäÕż¦õŠĀÕĖłÕģäŃĆéĶ░óĶ░óõĮĀµÄźÕÅŚµłæńÜäEĶ«┐ŃĆé -------------------- õĮĀõ╗¼ń£ŗķéŻÕż®õĖŖńÜäķŻ×ķĖ¤’╝īõ╣¤õĖŹń¦Ź’╝īõ╣¤õĖŹµöČ’╝īõ╣¤õĖŹń¦»ĶōäÕ£©õ╗ōķćī’╝īõĮĀõ╗¼ńÜäÕż®ńłČÕ░ÜõĖöÕģ╗µ┤╗Õ«āŃĆéõĮĀõ╗¼õĖŹµ»öķŻ×ķĖ¤Ķ┤ĄķćŹÕŠŚÕżÜÕÉŚ’╝¤õĮĀõ╗¼Õō¬õĖĆõĖ¬ĶāĮńö©µĆØĶÖæõĮ┐Õ»┐µĢ░ÕżÜÕŖĀõĖĆÕł╗Õæó’╝¤õĮĢÕ┐ģõĖ║ĶĪŻĶŻ│Õ┐¦ĶÖæÕæó’╝¤õĮĀµā│’╝īķćÄÕ£░ķćīńÜäńÖŠÕÉłĶŖ▒µĆÄõ╣łķĢ┐ĶĄĘµØź’╝īÕ«āõ╣¤õĖŹÕŖ│Ķŗ”’╝īõ╣¤õĖŹń║║ń║┐’╝īńäČĶĆīµłæÕæŖĶ»ēõĮĀõ╗¼’╝ÜÕ░▒µś»µēĆńĮŚķŚ©µ×üĶŹŻÕŹÄńÜ䵌ČÕĆÖ’╝īõ╗¢µēĆń®┐µł┤ńÜäĶ┐śõĖŹÕ”éĶ┐ÖĶŖ▒õĖƵ£ĄÕæó’╝üõĮĀõ╗¼Ķ┐ÖÕ░Åõ┐ĪńÜäõ║║Õō¬’╝īķćÄÕ£░ķćīńÜäĶŹēõ╗ŖÕż®Ķ┐śÕ£©’╝īµśÄÕż®Õ░▒õĖóÕ£©ńéēķćī’╝īńź×Ķ┐śń╗ÖÕ«āĶ┐ÖµĀĘńÜäÕ”åķź░’╝īõĮĢÕåĄõĮĀõ╗¼Õæó’╝¤ ŌĆöŌĆöŃĆŖķ®¼Õż¬ń”Åķ¤│ŃĆŗń¼¼ÕģŁń½Ā
|
 2007-01-31 17:30 2007-01-31 17:30
ķōŠµÄź:
#3
|
|
|
µ¢░ķĖ¤ÕģźķŚ©  ń╗äÕł½: µ│©Õåīõ╝ÜÕæś ÕĖ¢ÕŁÉ: 30 µ│©Õåī: 2006-12-25 ń╝¢ÕÅĘ: 1859 |
Õ╝Ģńö© (µ│Įķøē @ 2007-01-30 21:55 ) ĶĪźÕģģĶ»┤µśÄõĖĆÕÅź’╝Ü õĖŖķØóµ¢ćń½ĀÕÉÄµØźÕÅæĶĪ©Õ£©ŃĆŖõ║║µ░æķ¤│õ╣ÉŃĆŗ2005Õ╣┤ń¼¼7µ£¤ŃĆé Õ£©ŌĆ£ńł▒õ╣Éõ║║ķÜÅń¼öŌĆØĶ«║ÕØøõĖŖ’╝īµłæĶ┐śµøŠÕ░▒ķś┐ķĢŚÕģłńö¤ńÜäŃĆŖńź×ķøĢõŠĀõŠŻõ║żÕōŹõ╣ÉŃĆŗĶ»┤Ķ┐ćõĖŗķØóõĖƵ«ĄĶ»Ø’╝Ü µłæĶ┐śµā│Ķ»┤’╝īÕźćµĆ¬ńÜ䵜»’╝īÕÉ¼Õł½ńÜäõ║żÕōŹõ╣É’╝īµŚĀĶ«║Õøóķś¤ńÜäÕÉłõĮ£µś»Õ”éõĮĢńÜäµ┐ĆÕŖ©õ║║Õ┐ā’╝īµłæµĆ╗µś»Ķ┐½ÕłćÕ£░µ£¤ÕŠģńØĆķ鯵£ĆńŠÄµ£ĆńŠÄńÜäõĖƵ«ĄµŚŗÕŠŗÕć║µØź’╝īńäČÕÉÄÕ░▒µ╗ĪĶČ│õ║å’╝īńäČÕÉÄÕ░▒Õ£©ÕŹāÕåøõĖćķ®¼ÕźöĶģŠńÜäŌĆ£ÕÆŻŌĆöŌĆöÕÆŻŌĆöŌĆöÕÆŻŌĆöŌĆöŌĆØõĖŁÕŠŚÕł░õ║åµāģµä¤ÕŹćÕŹÄŃĆéµ»ÅÕø×Õɼ’╝īµēƵ£¤ÕŠģńÜäµĆ╗µś»Õø║Õ«ÜõĖŹÕÅś’╝īķØ×ÕĖĖõĖōõĖĆŃĆéĶĆīÕɼķś┐ķĢŚ’╝īÕŹ┤µĆ╗µś»µ░┤µĆ¦µē¼ĶŖ▒ŃĆüń¦╗µāģÕł½µüŗ’╝Üõ╗ŖÕż®µś»µ£¤ÕŠģÕ░ÅķŠÖÕź│õĖ╗ķóś’╝īõ╗╗Õ棵Ģ┤õ╗śÕ┐āĶéØń╗ÖµŚŗÕŠŗµÉōÕŠŚĶĮ»ń╗Ąń╗ĄńÜä’╝øµśÄÕż®µś»µ£¤ÕŠģķāŁĶźäõĖ╗ķóś’╝īõ╗żµłæĶāĪµĆØõ╣▒µā│Ķ«░ĶĄĘõĮÖÕģČõ╝¤ńÜäķ½śĶāĪ’╝īÕø×Õæ│õĖĵ¼ŻĶĄÅĶć¬ÕĘ▒ķØ×ÕĖĖń夵éēńÜäÕ╣┐õĖ£õ║║ńÜäµĆ¦µĀ╝’╝łµłæµ▓ĪĶ»╗Ķ┐ćÕ░ÅĶ»┤’╝īõĖŹń¤źķāŁĶźäµĆ¦µĀ╝µś»µĆĵĀĘńÜä’╝īµłæÕå│Õ«ÜÕ┐ÖÕ«īÕĮĢķ¤│ÕĘźõĮ£ÕÉÄÕ░▒õ╣░Õ░ÅĶ»┤µØźĶ»╗’╝ē’╝øÕÉÄÕż®ÕŹ┤ÕÅłµ£¤ÕŠģµØ©Ķ┐ćõĖ╗ķóś’╝īµä¤ÕÅŚńØĆõ╗¢ńÜäÕÅŹÕÅø’╝īµä¤ÕŖ©ńØĆõ╗¢ńÜäń║»µāģ’╝øµ£ĆĶ┐æõĖżÕż®’╝īµłæÕŹ┤Ķó½ķāŁķØ¢ķéŻÕłÜµĆ¦ÕŹüĶČ│ńÜäõĖ╗ķóśÕĮ╗Õ║ĢÕŠüµ£Źõ║å’╝īµĢ┤õĖ¬ńÜäńüĄķŁéÕźĮÕāÅÕ£©ń®║µ░öõĖŁķŻśńØĆ’╝īµĆÄõ╣łõ╣¤ĶÉĮõĖŹõĖŗµØźŃĆéÕåŹĶ┐ćÕćĀÕż®’╝īµłæõ╝ܵĆÄõ╣łµĀĘ’╝īĶ┐śµ£¬ÕÅ»ń¤źŃĆéÕŬĶ”üõĖŹõ╝ÜÕŠŚńź×ń╗ÅńŚģÕ░▒ĶĪīõ║åŃĆé |
ń»ćÕĖ¢ÕŁÉÕ£©Ķ┐ÖõĖ¬õĖ╗ķóś
 µ│Įķøē ÕŻ░ńÄ»µø▓ÕćåÕżćĶ«®õĮĀńÜäõ║║ĶłīÕÅśµłÉķĖ¤Ķłī 2007-01-07 03:18
µ│Įķøē ÕŻ░ńÄ»µø▓ÕćåÕżćĶ«®õĮĀńÜäõ║║ĶłīÕÅśµłÉķĖ¤Ķłī 2007-01-07 03:18
 µ│Įķøē ńÄ░Õ£©µłæÕ░åŃĆŖÕŚōķ¤│ńÜäń¦æÕŁ”Ķ«Łń╗āõĖÄõ┐ØÕüźŃĆŗńÜ... 2007-01-07 03:25
µ│Įķøē ńÄ░Õ£©µłæÕ░åŃĆŖÕŚōķ¤│ńÜäń¦æÕŁ”Ķ«Łń╗āõĖÄõ┐ØÕüźŃĆŗńÜ... 2007-01-07 03:25
 µ│Įķøē ĶĘŗ’╝ÜķĆüõĮĀõĖĆÕźŚÕüźÕŻ░µōŹ
Õ░ŵŚČÕĆÖ’╝īÕŹ░Ķ▒Īµ£Ć... 2007-01-07 03:27
µ│Įķøē ĶĘŗ’╝ÜķĆüõĮĀõĖĆÕźŚÕüźÕŻ░µōŹ
Õ░ŵŚČÕĆÖ’╝īÕŹ░Ķ▒Īµ£Ć... 2007-01-07 03:27
 µ│Įķøē ńø« ÕĮĢ
Õ»╝Ķ©Ć’╝ÜÕŚōķ¤│õĖÄõ║║ńö¤
ńö©µ░öÕÅæÕŻ... 2007-01-07 03:27
µ│Įķøē ńø« ÕĮĢ
Õ»╝Ķ©Ć’╝ÜÕŚōķ¤│õĖÄõ║║ńö¤
ńö©µ░öÕÅæÕŻ... 2007-01-07 03:27
 Õ▓®ķ╣Ł Õż¬ÕźĮõ║å’╝īµ¼óĶ┐ÄÕŻ░ńÄ»µø▓ĶĆüÕĖłµØźÕÄ”ķŚ©’╝ü
õĖŹ... 2007-01-07 03:29
Õ▓®ķ╣Ł Õż¬ÕźĮõ║å’╝īµ¼óĶ┐ÄÕŻ░ńÄ»µø▓ĶĆüÕĖłµØźÕÄ”ķŚ©’╝ü
õĖŹ... 2007-01-07 03:29

 Õ▒▒ķ╣░ Õ╝Ģńö© (Õ▓®ķ╣Ł @ 2007-01-06 19:29 )Õż¬ÕźĮõ║å’... 2007-01-07 09:48
Õ▒▒ķ╣░ Õ╝Ģńö© (Õ▓®ķ╣Ł @ 2007-01-06 19:29 )Õż¬ÕźĮõ║å’... 2007-01-07 09:48
 ńī½Õż┤ķ╣░ ńź×õ║å~~ńź×õ║å~~~ ÕüȵŖźÕÉŹÕģł 2007-01-08 03:57
ńī½Õż┤ķ╣░ ńź×õ║å~~ńź×õ║å~~~ ÕüȵŖźÕÉŹÕģł 2007-01-08 03:57
 õĖŖÕ░ē Õż¬ÕźĮõ║å’╝ü...ńāŁńāłµ¼óĶ┐ÄÕŻ░ńÄ»µø▓ĶĆüÕĖłµŗ®µŚČĶÄ... 2007-01-08 14:06
õĖŖÕ░ē Õż¬ÕźĮõ║å’╝ü...ńāŁńāłµ¼óĶ┐ÄÕŻ░ńÄ»µø▓ĶĆüÕĖłµŗ®µŚČĶÄ... 2007-01-08 14:06
 Õ»źÕ»ź RE: ÕŻ░ńÄ»µø▓ÕćåÕżćĶ«®õĮĀńÜäõ║║ĶłīÕÅśµłÉķĖ¤Ķłī 2007-01-08 17:19
Õ»źÕ»ź RE: ÕŻ░ńÄ»µø▓ÕćåÕżćĶ«®õĮĀńÜäõ║║ĶłīÕÅśµłÉķĖ¤Ķłī 2007-01-08 17:19
 ńÄēń▒│ķ½śń▓▒ ÕŻ░ķ¤│-ńÄ»õ┐Ø-µŁīµø▓ĶĆüÕĖł,
ńø╝µ£øõĮĀµØźÕÄ”ķŚ©õĖŖĶ... 2007-01-08 17:30
ńÄēń▒│ķ½śń▓▒ ÕŻ░ķ¤│-ńÄ»õ┐Ø-µŁīµø▓ĶĆüÕĖł,
ńø╝µ£øõĮĀµØźÕÄ”ķŚ©õĖŖĶ... 2007-01-08 17:30

 ÕŻ░ńÄ»µø▓ µłæµś©Õż®Õł░õ║åµĄÖµ▒¤ÕĖłĶīāÕż¦ÕŁ”’╝īõ╗ŖÕż®ńÜäĶ»ŠÕ«... 2007-01-08 19:19
ÕŻ░ńÄ»µø▓ µłæµś©Õż®Õł░õ║åµĄÖµ▒¤ÕĖłĶīāÕż¦ÕŁ”’╝īõ╗ŖÕż®ńÜäĶ»ŠÕ«... 2007-01-08 19:19

 ÕŻ░ńÄ»µø▓ µ│ĮķøēńÜäÕ░üķØóÕøŠµś»õ╗ÄńĮæõĖŖµēŠńÜäÕɦŃĆ鵳æĶ┐Öķć... 2007-01-08 19:27
ÕŻ░ńÄ»µø▓ µ│ĮķøēńÜäÕ░üķØóÕøŠµś»õ╗ÄńĮæõĖŖµēŠńÜäÕɦŃĆ鵳æĶ┐Öķć... 2007-01-08 19:27

 µ│Įķøē Õ╝Ģńö© (ÕŻ░ńÄ»µø▓ @ 2007-01-08 11:19 )õ╗ŖµÖ©Ķ... 2007-01-09 00:44
µ│Įķøē Õ╝Ģńö© (ÕŻ░ńÄ»µø▓ @ 2007-01-08 11:19 )õ╗ŖµÖ©Ķ... 2007-01-09 00:44

 ÕŻ░ńÄ»µø▓ Õ╝Ģńö© (µ│Įķøē @ 2007-01-08 16:44 )Õ╝Ģńö© (ÕŻ... 2007-01-09 17:11
ÕŻ░ńÄ»µø▓ Õ╝Ģńö© (µ│Įķøē @ 2007-01-08 16:44 )Õ╝Ģńö© (ÕŻ... 2007-01-09 17:11
 ÕÅ░ÕīŚ Õż¬ÕźĮõ║å!
ńāŁńł▒Ķć¬ńäČńÜäõ║║õ╣¤Õ┐ģÕ«ÜńāŁńł▒ķ¤│õ╣É... 2007-01-08 20:28
ÕÅ░ÕīŚ Õż¬ÕźĮõ║å!
ńāŁńł▒Ķć¬ńäČńÜäõ║║õ╣¤Õ┐ģÕ«ÜńāŁńł▒ķ¤│õ╣É... 2007-01-08 20:28

 ÕŻ░ńÄ»µø▓ Õ╝Ģńö© (ÕÅ░ÕīŚ @ 2007-01-08 12:28 )Õż¬ÕźĮõ║å!... 2007-01-15 02:34
ÕŻ░ńÄ»µø▓ Õ╝Ģńö© (ÕÅ░ÕīŚ @ 2007-01-08 12:28 )Õż¬ÕźĮõ║å!... 2007-01-15 02:34

 ÕŻ░ńÄ»µø▓ Ķ░óĶ░óÕ▓®ķ╣ŁŃĆüÕ▒▒ķ╣░ŃĆüńī½Õż┤ķ╣░ŃĆüõĖŖÕ░ēŃĆüÕÅ░Õī... 2007-01-15 02:58
ÕŻ░ńÄ»µø▓ Ķ░óĶ░óÕ▓®ķ╣ŁŃĆüÕ▒▒ķ╣░ŃĆüńī½Õż┤ķ╣░ŃĆüõĖŖÕ░ēŃĆüÕÅ░Õī... 2007-01-15 02:58
 ÕÅ░ÕīŚ ÕŻ░ńÄ»µø▓ĶĆüÕĖłÕ”éµ×£Õł░ÕÄ”ķŚ©µØźĶ«▓Ķ»Š,µłæÕģłµø┐µ... 2007-01-08 20:32
ÕÅ░ÕīŚ ÕŻ░ńÄ»µø▓ĶĆüÕĖłÕ”éµ×£Õł░ÕÄ”ķŚ©µØźĶ«▓Ķ»Š,µłæÕģłµø┐µ... 2007-01-08 20:32
 µ│Įķøē ÕÅ░ÕīŚĶ”üÕŁ”Õć║µØź’╝īĶĄĘńĀüõĖŹõ╝ܵ£ēõ║║ÕåŹĶ»┤õĮĀµś... 2007-01-09 00:43
µ│Įķøē ÕÅ░ÕīŚĶ”üÕŁ”Õć║µØź’╝īĶĄĘńĀüõĖŹõ╝ܵ£ēõ║║ÕåŹĶ»┤õĮĀµś... 2007-01-09 00:43
 ńÄēń▒│ķ½śń▓▒ µ▓Īµ£ēńŁŠÕÉŹńÜäõ╣”,
Ķé»Õ«Üµś»ķĆüµłæńÜä,
haha,
Õ”éµ... 2007-01-09 16:37
ńÄēń▒│ķ½śń▓▒ µ▓Īµ£ēńŁŠÕÉŹńÜäõ╣”,
Ķé»Õ«Üµś»ķĆüµłæńÜä,
haha,
Õ”éµ... 2007-01-09 16:37
 Õ▓®ķ╣Ł Ķ░óĶ░óÕŻ░ńÄ»µø▓ĶĆüÕĖł’╝üń£ŗµØźÕż¦Õ«ČÕ»╣õ║ĵĆÄõ╣łµŖ... 2007-01-09 16:55
Õ▓®ķ╣Ł Ķ░óĶ░óÕŻ░ńÄ»µø▓ĶĆüÕĖł’╝üń£ŗµØźÕż¦Õ«ČÕ»╣õ║ĵĆÄõ╣łµŖ... 2007-01-09 16:55

 ÕĆÖķĖ¤ Õ╝Ģńö© (Õ▓®ķ╣Ł @ 2007-01-09 08:55 )Ķ░óĶ░óÕŻ░ń... 2007-01-10 09:18
ÕĆÖķĖ¤ Õ╝Ģńö© (Õ▓®ķ╣Ł @ 2007-01-09 08:55 )Ķ░óĶ░óÕŻ░ń... 2007-01-10 09:18
 ńīÄÕĮ▒ Õ╝║ńāłĶ”üµ▒éÕŻ░ńÄ»µø▓ĶĆüÕĖłµØźĶÄåńö░ÕŖĀµ╝öõĖĆÕ£║’╝... 2007-01-10 07:02
ńīÄÕĮ▒ Õ╝║ńāłĶ”üµ▒éÕŻ░ńÄ»µø▓ĶĆüÕĖłµØźĶÄåńö░ÕŖĀµ╝öõĖĆÕ£║’╝... 2007-01-10 07:02
 µ│Įķøē ÕŻ░ńÄ»µø▓ĶĆüÕĖłõ╗źÕÉÄÕ░▒ń¤źķüōõ║å’╝īŌĆ£õĖŁµ»ÆŌĆØÕÄ... 2007-01-10 17:06
µ│Įķøē ÕŻ░ńÄ»µø▓ĶĆüÕĖłõ╗źÕÉÄÕ░▒ń¤źķüōõ║å’╝īŌĆ£õĖŁµ»ÆŌĆØÕÄ... 2007-01-10 17:06
 õ║æķ╣ż ńÄ░Õ£©µēŹµ│©µäÅÕł░Ķ┐ÖĶ┤┤’╝īµłæÕ¢ēÕÆÖńē╣ńāé’╝īńē╣Õł... 2007-01-15 03:20
õ║æķ╣ż ńÄ░Õ£©µēŹµ│©µäÅÕł░Ķ┐ÖĶ┤┤’╝īµłæÕ¢ēÕÆÖńē╣ńāé’╝īńē╣Õł... 2007-01-15 03:20
 ńćĢķĖź ÕŻ░ńÄ»µø▓ĶĆüÕĖłńÜäõ╣”Õł░õ║åÕÉŚ’╝¤µłæÕŠłµā│Ķ”üõĖĆÕź... 2007-01-15 03:21
ńćĢķĖź ÕŻ░ńÄ»µø▓ĶĆüÕĖłńÜäõ╣”Õł░õ║åÕÉŚ’╝¤µłæÕŠłµā│Ķ”üõĖĆÕź... 2007-01-15 03:21

 ÕŻ░ńÄ»µø▓ Õ╝Ģńö© (ńćĢķĖź @ 2007-01-14 19:21 )ÕŻ░ńÄ»µø▓Ķ... 2007-01-15 19:01
ÕŻ░ńÄ»µø▓ Õ╝Ģńö© (ńćĢķĖź @ 2007-01-14 19:21 )ÕŻ░ńÄ»µø▓Ķ... 2007-01-15 19:01


 ńćĢķĖź Õ╝Ģńö© (ÕŻ░ńÄ»µø▓ @ 2007-01-15 11:01 )Õ╝Ģńö© ... 2007-01-15 19:02
ńćĢķĖź Õ╝Ģńö© (ÕŻ░ńÄ»µø▓ @ 2007-01-15 11:01 )Õ╝Ģńö© ... 2007-01-15 19:02

 µ│Įķøē Õ╝Ģńö© (ńćĢķĖź @ 2007-01-14 19:21 )ÕŻ░ńÄ»µø▓Ķ... 2007-01-16 03:33
µ│Įķøē Õ╝Ģńö© (ńćĢķĖź @ 2007-01-14 19:21 )ÕŻ░ńÄ»µø▓Ķ... 2007-01-16 03:33

 ńćĢķĖź Õ╝Ģńö© (µ│Įķøē @ 2007-01-15 19:33 )Õ╝Ģńö© (ńć... 2007-01-16 03:43
ńćĢķĖź Õ╝Ģńö© (µ│Įķøē @ 2007-01-15 19:33 )Õ╝Ģńö© (ńć... 2007-01-16 03:43

 ÕŻ░ńÄ»µø▓ µä¤Ķ░óµ│ĮķøēķĆüń╗ÖµłæŃĆŖõĖŁÕøĮķĖ¤ń▒╗ķćÄÕż¢µēŗÕåīŃĆ... 2007-01-16 20:42
ÕŻ░ńÄ»µø▓ µä¤Ķ░óµ│ĮķøēķĆüń╗ÖµłæŃĆŖõĖŁÕøĮķĖ¤ń▒╗ķćÄÕż¢µēŗÕåīŃĆ... 2007-01-16 20:42
 Õ▓®ķ╣Ł ÕŻ░ńÄ»µø▓ĶĆüÕĖłĶĄĀķĆüķĖ¤õ╝ÜńÜäõ╣”ÕĘ▓ń╗ŵöČÕł░’╝īķØ... 2007-01-15 16:22
Õ▓®ķ╣Ł ÕŻ░ńÄ»µø▓ĶĆüÕĖłĶĄĀķĆüķĖ¤õ╝ÜńÜäõ╣”ÕĘ▓ń╗ŵöČÕł░’╝īķØ... 2007-01-15 16:22
 ńÄēń▒│ķ½śń▓▒ ķ”¢µ¼ĪÕ«ÜĶ┤Łõ╣░5µ£¼. 2007-01-16 21:07
ńÄēń▒│ķ½śń▓▒ ķ”¢µ¼ĪÕ«ÜĶ┤Łõ╣░5µ£¼. 2007-01-16 21:07
 ķćÄķĖ¤ Ķ«óĶ┤Ł2µ£¼ 2007-01-16 21:31
ķćÄķĖ¤ Ķ«óĶ┤Ł2µ£¼ 2007-01-16 21:31
 ÕŻ░ńÄ»µø▓ Ķ░óĶ░óńÄēń▒│ķ½śń▓▒ÕÆīķćÄķĖ¤ŃĆéÕłÜµēŹµłæĶ»ĢÕøŠĶ┤┤õĖ... 2007-01-16 21:59
ÕŻ░ńÄ»µø▓ Ķ░óĶ░óńÄēń▒│ķ½śń▓▒ÕÆīķćÄķĖ¤ŃĆéÕłÜµēŹµłæĶ»ĢÕøŠĶ┤┤õĖ... 2007-01-16 21:59
 õĖēńÜ« Ķ┐ćÕż¦ńÜäµ¢ćõ╗ČÕÅ»õ╗źÕ░ØĶ»ĢÕÄŗń╝®µłÉÕłåÕŹĘńÜärarõĖ... 2007-01-17 03:27
õĖēńÜ« Ķ┐ćÕż¦ńÜäµ¢ćõ╗ČÕÅ»õ╗źÕ░ØĶ»ĢÕÄŗń╝®µłÉÕłåÕŹĘńÜärarõĖ... 2007-01-17 03:27
 õĖŹń¤źķüō õĖĆõĖ¬µ¢░ńÜ䵌ģń©ŗ. 2007-01-17 20:45
õĖŹń¤źķüō õĖĆõĖ¬µ¢░ńÜ䵌ģń©ŗ. 2007-01-17 20:45
 õĖŖÕ░ē ķØ×ÕĖĖµä¤Ķ░óÕŻ░ńÄ»µø▓ĶĆüÕĖł’╝üµłæµ£ĆĶ┐æÕ£©µŗ£Ķ»╗µé... 2007-01-18 00:51
õĖŖÕ░ē ķØ×ÕĖĖµä¤Ķ░óÕŻ░ńÄ»µø▓ĶĆüÕĖł’╝üµłæµ£ĆĶ┐æÕ£©µŗ£Ķ»╗µé... 2007-01-18 00:51

 ÕŻ░ńÄ»µø▓ Õ╝Ģńö© (õĖŖÕ░ē @ 2007-01-17 16:51 )ķØ×ÕĖĖµä¤Ķ... 2007-01-18 17:19
ÕŻ░ńÄ»µø▓ Õ╝Ģńö© (õĖŖÕ░ē @ 2007-01-17 16:51 )ķØ×ÕĖĖµä¤Ķ... 2007-01-18 17:19

 Õ▓®ķ╣Ł Õ╝Ģńö© (ÕŻ░ńÄ»µø▓ @ 2007-01-18 09:19 )Õ╝Ģńö© ... 2007-01-19 00:55
Õ▓®ķ╣Ł Õ╝Ģńö© (ÕŻ░ńÄ»µø▓ @ 2007-01-18 09:19 )Õ╝Ģńö© ... 2007-01-19 00:55
 ÕŻ░ńÄ»µø▓ õĖŖµÄźÕĮĢķ¤│1 2007-01-18 17:34
ÕŻ░ńÄ»µø▓ õĖŖµÄźÕĮĢķ¤│1 2007-01-18 17:34
 ÕŻ░ńÄ»µø▓ õĖŖµÄźÕĮĢķ¤│2 2007-01-18 17:37
ÕŻ░ńÄ»µø▓ õĖŖµÄźÕĮĢķ¤│2 2007-01-18 17:37
 ńÄēń▒│ķ½śń▓▒ µŹ«Ķ»┤ÕīŚõ║¼õĖŁÕøĮńÜäõĖĆõĖ¬ńÄ»Õóāõ┐صŖżÕøóķś¤’╝ī
õ... 2007-01-22 20:29
ńÄēń▒│ķ½śń▓▒ µŹ«Ķ»┤ÕīŚõ║¼õĖŁÕøĮńÜäõĖĆõĖ¬ńÄ»Õóāõ┐صŖżÕøóķś¤’╝ī
õ... 2007-01-22 20:29

 Õ▓®ķ╣Ł Õ╝Ģńö© (ńÄēń▒│ķ½śń▓▒ @ 2007-01-22 12:29 )µŹ«Ķ... 2007-01-22 20:31
Õ▓®ķ╣Ł Õ╝Ģńö© (ńÄēń▒│ķ½śń▓▒ @ 2007-01-22 12:29 )µŹ«Ķ... 2007-01-22 20:31

 ńćĢķĖź Õ╝Ģńö© (Õ▓®ķ╣Ł @ 2007-01-22 12:31 )Õ╝Ģńö© (ńÄ... 2007-01-22 20:38
ńćĢķĖź Õ╝Ģńö© (Õ▓®ķ╣Ł @ 2007-01-22 12:31 )Õ╝Ģńö© (ńÄ... 2007-01-22 20:38
 ńÄēń▒│ķ½śń▓▒ õ╗¢õ╗¼ńÜäÕÉŹÕŁŚÕ░▒µś»Ķć¬ńäČõ╣ŗÕÅŗ’╝ī
Ķ¦éķĖ¤µś»Õøóķ... 2007-01-22 21:31
ńÄēń▒│ķ½śń▓▒ õ╗¢õ╗¼ńÜäÕÉŹÕŁŚÕ░▒µś»Ķć¬ńäČõ╣ŗÕÅŗ’╝ī
Ķ¦éķĖ¤µś»Õøóķ... 2007-01-22 21:31
 ÕŻ░ńÄ»µø▓ õĖŖÕ橵łæÕĘ▓ĶʤõĖŖµĄĘķ¤│õ╣ÉÕŁ”ķÖóÕć║ńēłńżŠĶüöń│╗’╝... 2007-01-30 17:23
ÕŻ░ńÄ»µø▓ õĖŖÕ橵łæÕĘ▓ĶʤõĖŖµĄĘķ¤│õ╣ÉÕŁ”ķÖóÕć║ńēłńżŠĶüöń│╗’╝... 2007-01-30 17:23

 Õ▓®ķ╣Ł Õ╝Ģńö© (ÕŻ░ńÄ»µø▓ @ 2007-01-30 09:23 )õĖŖÕ橵... 2007-01-30 18:27
Õ▓®ķ╣Ł Õ╝Ģńö© (ÕŻ░ńÄ»µø▓ @ 2007-01-30 09:23 )õĖŖÕ橵... 2007-01-30 18:27
 ÕŻ░ńÄ»µø▓ ÕÅ░µ╣ŠõĮ£µø▓Õ«Čķś┐ķĢŚÕģłńö¤ńÜäŃĆŖµ£©ńō£ŃĆŗ’╝īµś»õ╗... 2007-01-30 17:28
ÕŻ░ńÄ»µø▓ ÕÅ░µ╣ŠõĮ£µø▓Õ«Čķś┐ķĢŚÕģłńö¤ńÜäŃĆŖµ£©ńō£ŃĆŗ’╝īµś»õ╗... 2007-01-30 17:28
 ńÄēń▒│ķ½śń▓▒ Ķ░óĶ░óÕŻ░ńÄ»µø▓ĶĆüÕĖł’╝ī
õĮĀµØźÕÄ”ķŚ©ńÜ䵌ČÕĆÖ’╝ī
... 2007-01-30 17:30
ńÄēń▒│ķ½śń▓▒ Ķ░óĶ░óÕŻ░ńÄ»µø▓ĶĆüÕĖł’╝ī
õĮĀµØźÕÄ”ķŚ©ńÜ䵌ČÕĆÖ’╝ī
... 2007-01-30 17:30

 ÕŻ░ńÄ»µø▓ Õ╝Ģńö© (ńÄēń▒│ķ½śń▓▒ @ 2007-01-30 09:30 )Ķ░óĶ... 2007-01-30 17:47
ÕŻ░ńÄ»µø▓ Õ╝Ģńö© (ńÄēń▒│ķ½śń▓▒ @ 2007-01-30 09:30 )Ķ░óĶ... 2007-01-30 17:47
 ÕŻ░ńÄ»µø▓ õĖŗķØóĶ┐Öķ”¢ŃĆŖķØÖÕż£µĆØŃĆŗ’╝īķĆéÕÉłńŗ¼Õö▒’╝īõ╣¤ķĆ... 2007-01-30 17:38
ÕŻ░ńÄ»µø▓ õĖŗķØóĶ┐Öķ”¢ŃĆŖķØÖÕż£µĆØŃĆŗ’╝īķĆéÕÉłńŗ¼Õö▒’╝īõ╣¤ķĆ... 2007-01-30 17:38
 ÕŻ░ńÄ»µø▓ õĖŗķØóĶ┐Öķ”¢ŃĆŖµ░┤Ķ░āµŁīÕż┤ŃĆŗ’╝īķĆéÕÉłńö©Õ╣┐ÕĘ×Ķ»... 2007-01-30 17:39
ÕŻ░ńÄ»µø▓ õĖŗķØóĶ┐Öķ”¢ŃĆŖµ░┤Ķ░āµŁīÕż┤ŃĆŗ’╝īķĆéÕÉłńö©Õ╣┐ÕĘ×Ķ»... 2007-01-30 17:39
 ÕŻ░ńÄ»µø▓ ŃĆŖµ░┤Ķ░āµŁīÕż┤ŃĆŗń¼¼2ķĪĄ 2007-01-30 17:41
ÕŻ░ńÄ»µø▓ ŃĆŖµ░┤Ķ░āµŁīÕż┤ŃĆŗń¼¼2ķĪĄ 2007-01-30 17:41
 ÕŻ░ńÄ»µø▓ ŃĆŖµ░┤Ķ░āµŁīÕż┤ŃĆŗń¼¼3ķĪĄ 2007-01-30 17:42
ÕŻ░ńÄ»µø▓ ŃĆŖµ░┤Ķ░āµŁīÕż┤ŃĆŗń¼¼3ķĪĄ 2007-01-30 17:42
 ÕŻ░ńÄ»µø▓ ŃĆŖµ░┤Ķ░āµŁīÕż┤ŃĆŗń¼¼4ķĪĄ 2007-01-30 17:42
ÕŻ░ńÄ»µø▓ ŃĆŖµ░┤Ķ░āµŁīÕż┤ŃĆŗń¼¼4ķĪĄ 2007-01-30 17:42
 ÕŻ░ńÄ»µø▓ ŃĆŖµ░┤Ķ░āµŁīÕż┤ŃĆŗń¼¼5ķĪĄ 2007-01-30 17:43
ÕŻ░ńÄ»µø▓ ŃĆŖµ░┤Ķ░āµŁīÕż┤ŃĆŗń¼¼5ķĪĄ 2007-01-30 17:43
 µ│Įķøē ÕƤµ£║ÕÅ»õ╗źń╗ÖÕż¦Õ«Čõ╗ŗń╗ŹõĖĆõĖŗķś┐ķĢŚÕģłńö¤ńÜäŃĆ... 2007-01-31 05:48
µ│Įķøē ÕƤµ£║ÕÅ»õ╗źń╗ÖÕż¦Õ«Čõ╗ŗń╗ŹõĖĆõĖŗķś┐ķĢŚÕģłńö¤ńÜäŃĆ... 2007-01-31 05:48
 µ│Įķøē ńÉ┤ÕÅ░Õ«óĶüÜ’╝ÜÕ╗┐Õģ½Õ╣┤ńŻ©µłÉńÜäŃĆīńź×õ╣ÉŃĆŹ
ÕĮ”... 2007-01-31 05:52
µ│Įķøē ńÉ┤ÕÅ░Õ«óĶüÜ’╝ÜÕ╗┐Õģ½Õ╣┤ńŻ©µłÉńÜäŃĆīńź×õ╣ÉŃĆŹ
ÕĮ”... 2007-01-31 05:52
 Õ▓®ķ╣Ł ÕɼĶ┐Öõ╗ŗń╗Źń£¤ńÜäÕŠłµā│ÕÉ¼ÕŻ░ńÄ»µø▓ĶĆüÕĖłńÜäĶ»Šõ║... 2007-01-31 18:25
Õ▓®ķ╣Ł ÕɼĶ┐Öõ╗ŗń╗Źń£¤ńÜäÕŠłµā│ÕÉ¼ÕŻ░ńÄ»µø▓ĶĆüÕĖłńÜäĶ»Šõ║... 2007-01-31 18:25
 Õ▒▒ķ╣░ µłæõĖŗĶĮĮÕɼõ║å’╝īõĖŹĶ┐ćõĖŹÕ░ÅÕ┐āĶ«ŠńĮ«µłÉÕŹĢµø▓ÕŠ... 2007-01-31 18:50
Õ▒▒ķ╣░ µłæõĖŗĶĮĮÕɼõ║å’╝īõĖŹĶ┐ćõĖŹÕ░ÅÕ┐āĶ«ŠńĮ«µłÉÕŹĢµø▓ÕŠ... 2007-01-31 18:50
 ńÄēń▒│ķ½śń▓▒ Õåģķā©µČłµü»’╝Ü
µ»Åµś¤µ£¤õĖƵÖÜõĖŖ7’╝Ü00’╝ī
Õ£©ÕÄ... 2007-01-31 21:00
ńÄēń▒│ķ½śń▓▒ Õåģķā©µČłµü»’╝Ü
µ»Åµś¤µ£¤õĖƵÖÜõĖŖ7’╝Ü00’╝ī
Õ£©ÕÄ... 2007-01-31 21:00
 Õ▓®ķ╣Ł ÕŻ░ńÄ»µø▓ĶĆüÕĖłÕ»äµØźńÜäõ╣”µöČÕł░õ║å’╝īõĖŗµ¼ĪÕĖ”ń╗... 2007-02-06 06:07
Õ▓®ķ╣Ł ÕŻ░ńÄ»µø▓ĶĆüÕĖłÕ»äµØźńÜäõ╣”µöČÕł░õ║å’╝īõĖŗµ¼ĪÕĖ”ń╗... 2007-02-06 06:07  |
1 õĮŹõ╝ÜÕæśµŁŻÕ£©ķśģĶ»╗µŁżõĖ╗ķóś (1 õĮŹµĖĖÕ«óÕÆī 0 õĮŹķÜÉĶ║½õ╝ÜÕæś)
0 õĮŹõ╝ÜÕæś:

| ń«ĆÕī¢ńēłµ£¼ | ÕĮōÕēŹµŚČķŚ┤: 2025-09-12 22:41 |
Powered By IP.Board
© 2025 IPS, Inc.
Licensed to: ┬®2006-2007 ÕÄ”ķŚ©Ķ¦éķĖ¤õ╝Ü, õĖŁÕø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