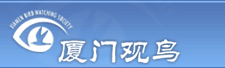2003-10-29 06:04 2003-10-29 06:04
链接:
#1
|
|
|
版主    组别: 版主 帖子: 789 注册: 2003-06-04 编号: 38 |
[几次考察之杂烩版]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将厦门岛吹拂得繁花似锦,特区建设的步伐在厦门岛东海域之滨的五通村,却似乎总是有些停滞。二十余年间,五通村的平静和困惑,与厦门岛的繁华与喧嚣,形成了两个世界。 随着东部开发的消息不断传来,行走五通的愿望忽然强烈起来。不错,再不及时记录昨日和今天的五通村,也许五通村就会象厦门许多已经消失的村庄一样,它的真实面目,终将无人知晓,湮没在流逝的岁月中。 主意已定,选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我约上厦门观鸟会一班热衷人文、生态科考的爱好者――岩鹭、斑鱼狗、上尉、拓比、蓝色鬼等人,开始我们的五通村考察之行。 -------------------- |
 |
回复
 2003-10-29 06:10 2003-10-29 06:10
链接:
#2
|
|
|
版主    组别: 版主 帖子: 789 注册: 2003-06-04 编号: 38 |
之二 龙门渡的传说与五通古渡头
八百多年前的一天,风急浪高,一艘木船从对岸颠簸而来,匆匆靠上五通渡头。几位风尘仆仆、身着官袍的男子跳下船来,小心翼翼地躬身将两个年约十岁的小孩迎上台阶,顾不上久留,两名中年男子就背上小孩,慌慌张张地离去。其中一名大官模样的男子临走还不忘提笔在渡头附近的两块巨石上写下“龙门”两字。 这个大官模样的男子,据说就是历史上那个“留取丹青作汗心”的文天祥。《同安县志》、《泉州府志》都这么说了,南宋恭宗德佑二年三月间,元兵攻破了南宋的都城临安城,逃难至福建的十一岁的赵晸称帝做了端宗。可惜,帝位还没坐热,元兵就已经南下,小皇帝只好在文天祥丞相的护卫下,与他的弟弟,八岁的卫王赵昺亡命南逃,急急如丧家之犬,过泉州又被拒之城外,一路狼狈,奔至同安,再从浏五店码头渡海逃上了厦门岛(那时还叫做嘉禾屿)。上岸的地方,就是五通渡头,从此,五通渡头也被人称作龙门渡了。据说文天祥还提笔在渡头附近的两块巨石上写下“龙门”两字。 其实文天祥丞相是不曾奉南宋幼主南逃的,这不,素以严谨著称的《闽书》就提出了质疑,认为保护幼主南逃的应该是丞相陆秀夫和将军张世杰。争论之间,历史早已悠悠近千年。如今,“龙门”碑刻荡然无存(笔者注:云顶岩上现有“龙门”石刻,应与上述故事无关),幼帝已成追忆,当年的渡海故事,也早已化为百姓心中的传说,给五通古渡头增添了几许神秘,几分暇思。 然而传说之中,却不免折射出一个史实:五通,原来早就是厦门岛的交通要道了。这在《鹭江志》、《厦门志》也均有记载:五通渡头,厦往泉大路,过刘五店,水途三十里。 是的,曾几何时,五通确乎是厦门出岛通大陆的咽喉。数百年间,五通作为厦门岛古驿道的重要一站,迎来送往,见证着人世的沧桑。根据可考证的历史表明,古时,厦门岛上有两条驿道。一条驿道是自岛北隔海的集美铺下接高崎铺,下接莲坂铺,再下接和凤铺(即今大中路和镇邦路之间的和凤街位置)。另一条驿道,就在厦门岛东北角设五通铺,上接过海的刘五店铺,下接蛟塘铺(又名“勾塘铺”,社名蛟塘即现在昭塘自然村),再下接金鸡亭铺、和凤铺,官府公文就在和凤铺交由船户带往金门、台湾等地投递。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政府在厦门岛建城时,同时在五通也建造了城寨,“徙永宁卫中、左千户所官军守御”。郑成功时期,五通更被视作战略要地。1655年农历四月,郑成功派人筑造了一批营寨,其中就有五通寨。在郑成功抗清的若干重要战役中,五通寨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中期以后,五通寨已圮,但仍设有五通讯,有了望台和墩台,清政府派“提标左营弁兵防守”。 乾隆二十六年之后(1761年),高崎铺因“铺务稀少裁汰”,五通渡口遂成为厦门出岛通往内陆的唯一口岸了。其后,厦门对台运输、贸易日益频繁,五通港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厦门志.台运略》作了清楚的描述:康熙二十四年以后,台湾船只往来,在内地惟厦门五通一口与鹿耳门一口对渡。由京城到台湾任职的官员,都得乘船到五通,再经蛟塘至和凤铺后,过海峡至台湾。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不知从何时起,五通渡头却“声渐悄”了。近现代以来,厦门的对外交通尤其是海上运输迅猛发展,五通码头作为曾经的交通要道却不曾有着相应的辉煌。我在近代以来描绘厦门对外交通的大量文字中,几乎找不到关于五通码头的描述。据说五通因当地供奉五通神得名,可惜,五通神并没有佑护五通走向辉煌,甚至连当年供奉五通神的五显宫,也被风雨吞噬地不知所终。历史的变迁,真是让人难以预料。 -------------------- |
篇帖子在这个主题
  |
1 位会员正在阅读此主题 (1 位游客和 0 位隐身会员)
0 位会员:

| 简化版本 | 当前时间: 2026-02-09 10:13 |
Powered By IP.Board
© 2026 IPS, Inc.
Licensed to: ©2006-2007 厦门观鸟会,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