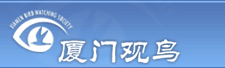|
 2007-12-06 23:04 2007-12-06 23:04
链接:
#1
|
|
 版主    组别: 版主 帖子: 13982 注册: 2003-05-31 编号: 18 |
我小的时候不知道鱼会生病,鸟会中毒,小孩子会死。但是我的父亲知道。他是一个生物学家。后来我父亲死了。我父亲的学生告诉我,长江的鱼不能吃了;在江边白茅上飞著的鸟儿,飞著飞著就摔下来死了,是铅中毒;在长江边出生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就得了肝癌。
在人们还没有反映过来为什么的时候,那条从天际流进诗里和画里的长江,突然丧失了衬托落霞孤骛的闲情逸志;突然关闭了博揽千帆万木的宽阔胸怀。长江,突然变成了我们的“敌人”。 在我最近一次回到江南的时候,我看见长江浑黄的水闷声不响地流著,象一个固执的老人,拖著一根扭曲的桃木拐棍,怨恨地从他的不肖子孙门前走过,再也不回头了。 这时候,我感到,我必须告诉长江和长江边的不肖子孙我父亲的故事。我父亲到死对长江都是一步三回头。我希望等到人们总算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会想起我的这些故事。 一。鱼的故事 我父亲死在美国的亚里桑那州。他去世之前,我和我弟弟带著他旅行了一次。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旅行。他拍了很多他感兴趣的照片。回来后,他把这些照片一一贴在他的影集上,每张照片下还写上一两句话。象是笔记。每次,我翻开他这本最后旅行的影集,看著他拍的这些照片,他写在这些照片下的那些句子,就变成了一张张退了色的老照片插了进来,讲著一些关于父亲的故事。 譬如说,影集的第一页,贴著两张父亲在夏威夷阿拉乌玛海湾,用防水照相机在水下拍的鱼儿。那些红黄相间的热带鱼,身体扁扁的,象蒲扇,在海里煽动起一圈圈碧蓝的波纹,那波纹象一习习快活的小风,鼓动著旁边两根褐色的海草。热带鱼在水草间平静地游逸,逍遥自在。 父亲在这两张照片下写著:“鱼,鱼,长江葛州坝的鱼是要到上游产卵的。” 父亲象很多老人一样到美国来看望他的儿女。没来之前想我和弟弟想得很热切。才到一天,就说:“我最多只能呆一个月,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回去做呢。”我和我弟弟说:“您都退休了,那些重要的事情让您的研究生做去吧。”父亲说,“研究生威性不够,没人听他们的。”我和弟弟就笑,“您威性高,谁听您的?”父亲唉声叹气。但过了一分钟,又坚决地说:“长江鱼儿回游的时候,我一定要走。” 长江鱼儿回游的时候,我父亲从来都是要走的。这个规矩从70年代长江上建了葛州坝开始。 我记得我父亲的朋友老谷穿著一双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写字时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饭,父亲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袄唉声叹气地在小客厅转来转去。 “坝上的过鱼道没有用?”父亲问。 “没用。”老谷说。 “鱼不从过鱼道走?” 父问。 “不走。”老谷说。 “下游的鱼上不去了?”父亲又问。 “我刚从葛洲坝来。鱼都停在那里呢。”老谷说。 “造坝前,我早就跟他们说了,鱼不听人的命令的,鱼有鱼的规矩。”父亲说。 “葛洲坝的人还以为他们今年渔业大丰收呢。正抓鱼苗上坛腌呢。”老谷说。 “你快吃,吃了我们就走。”父亲说。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只觉得他们惶惶不安。象两个赶著救火的救火员。后来我知道了他们带著三个研究生去了葛州坝,在那“过鱼道”前想尽了办法,长江的鱼儿终於没能懂得人的语言,也看不明白指向“过鱼道”的路标,一条条傻呼呼地停在坝的下游,等著大坝开恩为它们让条生路。 最后,父亲和老谷这两个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著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坝去。并且,从此之后,年年到了鱼儿回游的时候,他们都要带著研究生去拉鱼兄弟一把,把鱼儿们运过坝去。这叫做“科研”工作。鱼儿每年都得回游,於是我父亲就得了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我父亲死在长江三峡大坝蓄水之前。要不然,他又会再多一个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我父亲说,“我们这些教授,做的只能是亡羊补牢的工作。“羊”没亡的时候,你再喊再叫也没人听。” 我们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民族,而且是只要眼前功利的民族。我们可以把属於我们子孙的资源提前拿来快快地挥霍掉或糟蹋掉。我们喜欢子孙满堂,可是我们的关爱最多沿及到孙子辈就嘎然而止。至於我们的曾孙,重孙有没有太阳和月亮,清风和蓝天,我们脚一蹬,眼睛一闭,眼不见心不烦。我们还大大咧咧地嘲笑杞人忧天。天怎么会塌下来呢?真是庸人自扰之。我们的这种好感觉来得无根无据,却理直气壮。 偏巧,我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忧天的杞人。只是比杞人还多了一个愚公移山的本领--带领徒孙一年一年移鱼不止。 二。鸭子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二页,贴的是一群鸭子的照片。那时候,我们在地图上看见有一个叫“天鹅湖”的地方。我们就带著父亲去了。我们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玉米地里开了三个小时的车,然后,就钻进了这片树林。没有风,一根根老藤静静地从树枝上挂下来,象还静止在远古的时间多年不刮的胡须,非常祥和地垂到满地的腐叶上。我们找到了这个“天鹅湖”。湖里其实并没有天鹅,却停了满满的一湖鸭子。一个挨一个,远看密密麻麻,象一个个灰色的小跳蚤。我们的狗想到湖边去喝水,一湖的鸭子突然吼叫起来,象士兵一样朝我们的狗列队游过来,保卫它们的领域。父亲哈哈大笑,拍了这张鸭子的照片。 在这张照片底下,他写了:“鸭子,上海浦东的鸭子是长江污染的证明。” 从七十年代末起,人们发现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肝癌的发病率非常高。父亲有个很好的研究生,叫黄成,是孤儿。父母都得肝癌死了。父亲时常给他一些零花钱。他们家有兄妹五个,相亲相爱,住在上海浦东地区。这个研究生读书期间,大哥也死了,还是肝癌。人们不知道原因。父亲就带著几个研究生开始了调查,研究为什么上海浦东地区肝癌发病率高。 父亲选择研究在长江下游生活的鸭子。那一段时间,不停地有一些鸭子被送到我们家来。家里小小的厨房,全是鸭屎味。我和弟弟踮著脚,捏著鼻子到厨房去找零食吃,什么油球,麻糕上都带著鸭屎臭。我妈跟我父亲吵,叫他把这些鸭子弄走。我父亲说:“弄到哪里去,总不能弄到大学办公室里养吧。” 后来研究鸭子的结果出来的,上海浦东,崇明岛一带的鸭子活到两年以上的多半都得了肝癌。结论很明显:长江下游水质严重污染。 1989年我父亲带著一个黑皮箱,去美国参加“国际水资源环保大会”。我和他的研究生黄成送他上飞机。他的黑皮箱里装著详细的长江下游流域水资源污染状况的证据和研究报告。父亲身穿著崭新的西装。那西装的裤腿高高卷到膝盖,脚下还蹬著一双解放鞋。我和黄成要求再三,要他把西装的裤腿放下来,换上皮鞋。他说:“我整天在长江水里泡著,就习惯这样。”他就这样上了飞机。哪里象个教授。地道一个长江上的渔民。父亲半辈子都在长江上闯荡,象武打小说里的一条江湖好汉,替那些不能保护自己的长江水资源打抱不平。 父亲从美国开会回来,并不高兴。他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告,谈完污染就谈拯治措施。我报告完了污染,别人就问:你们国家的拯治措施是什么?我没法回答。我们没有。”那会是在十几年前开的。那时候环境保护还没有被中国人当作一回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在八,九十年代是挣钱。人们热衷于把自己的小家装璜得漂漂亮亮。一出小家门,门庭过道再脏也可以看不见。谁还会去管如何清理那些流到长江里,让鸭子得肝癌的东西。 去年,我在一个偶尔的机会碰见了父亲的研究生黄成。他到美国来短期访问。我问他:你好吗?他说:我来之前刚到上海去了一趟。我的最小的妹妹得肝癌去世了。於是,我们俩都同时怀念起我的父亲。 黄成回忆起我父亲写过的许多论文,做过的许多报告。那些论文和报告早早地就把长江水生资源的污染与危机呼吁出来了。不幸的是,在父亲有生之年,中国的社会先是只重视与天奋斗,与地奋斗,把人对自然的无知夸张成统治自然的权威;后来,社会又变成了是只重视向天要钱,向地要钱,把人的对自然的讹诈当做是从自然得来的财富。父亲象唐佶柯德,带著他的“桑丘”--几个衷心耿耿的研究生,向社会--这个转起来就不容易停的大风车宣战,到死都一直在孤军奋战。 3。船的故事 父亲影集的第三页,是我们在卡罗拉多河划船的照片。我和弟弟怕父亲在美国寂寞,怀念他在长江上的浪漫漂泊,决定带他到卡罗拉多河上去划船。卡罗拉多河水是浅绿色的,我们的小机动船是象牙色的,父亲高高兴兴地戴著渔民的草帽,把西装裤腿高高地卷过膝盖,笑眯眯地架著方向盘,象是回到了老家。象牙色的小机动船在水面上滑过,溅起高高低低的水珠,象一只灵巧的溜冰鞋在晶滢的水面上划过一道白色的印子。我记得当时,有一只麻雀一样的小鸟飞来停在船头,我弟弟就喂它面包吃。小鸟并不怕人,居然大大方方地走到我们放食物的椅子上自己招待起自己来。父亲感叹不已,说:“这种人和动物之间的信任不知要花多少代才能在中国建立。我们江南的麻雀见了人就象见了魔鬼一样。”我当然是很能理解父亲的意思。单靠几个科学家是拯救不了中国的动物危机和环境污染的。父亲在开船,他让我把他和小鸟还有船都照下来。 父亲在这张照片下写道:“要教育长江流域的老百姓。” 上海浦东的鸭子证明了长江被污染了后,我父亲就长年在长江的水域奔忙。他和他的研究生半年半年地住在渔民的船上收集资料。我和弟弟当时还小,就想混上渔船,到长江太湖溜达一圈。放暑假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一次。我记得我去的那条渔船很小,睡在后仓里,连我的腿都伸不直。一泡臭尿得憋到天黑,才能把屁股撅得高高地站在船沿上尿。那时候正是渔讯,船白天黑夜在水上颠簸。我父亲他们天不亮就起来在渔民打到的鱼堆里乱翻。他们把一些鱼作成切片,放在显微镜下面看。说是有些鱼脊椎弯了,有些鱼身上带血点,还有些鱼数量大减。 我在船上,百无聊奈,吃了一个星期没盐没油的鱼煮饭。下了地,连走路都象只青蛙,只会一颠一跳。后来,我再没有兴趣混上渔船玩了。我弟弟还混上去过一次。那次他们去的是太湖,船也大一点。我弟弟回来连说:“差点淹死,差点淹死。”以后也再不要去了。但是我父亲他们却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年又一年,到鱼汛的时候必走。紧密关注著长江流域的各种水生资源变化。后来他们干脆租了渔民的船,跟著鱼儿到处跑。从长江下游,一直到四川重庆,从太湖,一直到陂阳湖。他们跑遍了长江流域,年年如此,不管刮风下雨。他们也收集长江流域变了形的鸟,有一只麻雀类的鸟长了三个翅膀,第三个翅膀很小,象小孩子衣服上被扯破的小口袋。我和弟弟看著好玩,父亲说,这种变异可能也跟污染有关。 后来,父亲在N大学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大大小小污染变形鱼和其它长江流域常见动物的标本。我有时候到父亲的办公室去,看见这么多被污染鱼和动物的标本,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父亲和他的同事,研究生讨论起这些被污染鱼和动物,一个个的表情如兵临城下一般凝重。可长江沿岸的造纸厂和印刷厂依然往长江里排含铅的污水;肺结核病院和精神病院依然往长江里扔废弃的药品。父亲他们这些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到底能干什么呢。我甚至嘲笑父亲:“您的污染鱼和动物不到威胁国家政权稳定的时候,您那些对策都不会有人用的。” 父亲依然故我地在长江上忙碌。后来我发现父亲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父亲生命的意义。这种精神不可以用"献身"或"热爱"等形容词来描述。这种精神是一种冷静的理性,是一种负责任。是一种不仅仅对自己负责,而且对子孙后代负责,不仅仅对今天的发展负责,而且对人类所生存的地球的未来负责的精神。这是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为了这样一种科学和人文的精神,父亲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忍辱负重,在最没有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年代,做了许多直到今天,才被人们看出其重要意义的事情。 4。父亲追悼会的故事 父亲影集里的最后一张照片,是父亲追悼会的照片。那不是父亲贴上去的,是母亲贴上去的。母亲在照片下写了一行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取的是庄子<大宗师>里两条鱼的典故。小水塘里的水干涸了,最后的两条鱼往对方身上互相吐著水沫,以求一点湿润。人们感叹这是多伟大的爱情呀!可是对鱼来讲,还不如让它们快活地游在大江大湖里,而互相根本不用惦记著好。生死一别,父亲回归自然。 象其他许多中国贫穷而执著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样,父亲突然英年早逝了。那时候,他从那次最后的旅行回来不久。因为长江鱼儿回游的季节就快到了,他回中国的飞机票都卖好了。却终未能成行。父亲去世前几天全身的皮肤躁痒,后来突然胃出血,吐血不止。等救护车开到我们家的时候,父亲已经过去了。除了这本影集和每张照片下写的几行对长江恋恋不忘的句子,他没有遗言。 医生告诉我们他的死因可能是铅中毒。母亲什么话也没有说,在长江鱼儿回游的季节快到来之前带著父亲的骨灰按时回中国去了。父亲就这样回到了长江边。 父亲在美国对长江是一步三回头地依念,他的追悼会当然是应该在江南故里开。可母亲带著父亲的骨灰回到南京后,父亲系里的系主任非常愧疚地对母亲说:因为他们的书记倒期货,暗自动用了系里的钱。结果钱全砸进去赔了。连教授讲师当年的奖金都发不出,实在拿不出钱来给父亲开追悼会。结果,父亲的研究生黄成来了,当时就捐了三百块钱为父亲开追悼会,接著老谷也捐了,其他父亲的同事和学生都捐了钱。母亲哭了。 父亲的追悼会是在长江边开的,除了他的同事和学生,还有很多渔民。在追悼会上父亲的生平被连续起来: 父亲叫袁传宓,出身在江南的一个极富裕地主家庭,毕业于金陵大学。以后在N大学生物系工作了一辈子。他年轻的时候非常洋派,打领带,说英文,绝不是后来连西装都不会穿的"渔民"。他还会瞒著母亲把我和弟弟带到鸡鸣酒家楼上的西餐店去吃一份牛排。后来,文化大革命了,他下了农村,在农村养了几年猪。他跟所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一样,非常努力地把自己脑袋里祖宗八代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当作残渣剩汁统统抖落出来清洗干净,然后紧密地和工农打成一片。七十年代,一有正常工作的机会,他就全力为长江的环境保护奔走,呼喊,直到死亡。这就是父亲的一生。很简单。父亲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内心世界,他们的内心世界都得公开于众的。唯一还属于他们私人的就是一种根植于中国优秀知识分子良心中的科学和人文精神。这是父亲生命的支点. 父亲的故事讲完了。长江的故事还没有完,也许永远也不会完。最近老谷寄给我一份当地的报纸,上面报导了一个渔民捕到了一只长江珍稀动物白鲟。.报道里谈到,从渔民到科学家,大家都为抢救这只白鲟尽力。老谷看完之后,一定要他的儿子把这篇报道拿到我父亲的坟上去烧,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又因为长江里第一只白鲟是我父亲发现并命名的。那家报纸要我谈谈如果我父亲看见人们对珍稀动物如此关爱的事迹后会怎么想。这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九年了。终於,那种父亲一代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科学和人文的精神开始成为民众意识了。我父亲会怎么想呢? 我想,父亲大概会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父亲的科学家职业,让他能够比许多人看得远一点。与其到动物频临危机了,才来赞美人类对动物的关爱,不如不要干扰动物,让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也在地球上有一个位置,过它们和平的生活。地球不是我们人类独霸的,长江里的鱼儿有权力拒绝人类对它们的指挥或关爱。让动物按照它们各自物种的本能自由地生活,我想这可能是父亲会替鱼儿,鸟儿,鸭子,白鲟发表的独立宣言吧。 (本文获<侨报>2005年“五大道纪实文学”首奖,原载《美文 |
 2007-12-06 23:27 2007-12-06 23:27
链接:
#2
|
|
 版主    组别: 版主 帖子: 13982 注册: 2003-05-31 编号: 18 |
天价刀鱼之问(转)
无奈的讲述者 一张网,出水的长江刀鱼体似银刀,悲怆地垂死挣扎,网后是渔民的笑脸。这一切的背景是蓝色的渔船甲板、浑黄的长江、微茫的蓝天。 这是我为“长江刀鱼天价之问”组稿拍出的主图。采写结束一年多来,我的脑海里无数次出现这幕图景。回想的感觉于我,每次并不相同,这幅曾被业内夸赞的图片带给我的喜悦是短暂的。喜悦淡尽,我就有了像刀鱼一样的悲怆,以及与文中十多位刀鱼命运讲述者们相同的无奈。这组稿件带给我的感觉,如同这幅照片一样。 2005年4月中旬,我开始采访长江刀鱼组稿。采前,长江刀鱼与我这个内蒙古人来说是陌生的,我没见过更没吃过长江刀鱼。压力是较大的,因为这是我到新京报采写的第一篇稿件。我唯一的优势是,我在南京曾呆过三年,对长江中下游有着一定程度的熟悉。 我首先来到南京,我决心写一篇鱼的故事,思路是让与这条鱼相关的各类人共同讲述这个故事。但是,我不知道从何讲起。我专门去了一趟江边,我总在想,鱼儿在水里过得怎样呢? 通过圈内的朋友,我首先获知的是,一家位于无锡的水产科研部门正在作关于刀鱼的工作。在这里,我接触到了最重要的刀鱼讲述者之一——施炜纲,他的一个职务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资源研究室主任,据该单位告知,施即将担任该中心长江刀鱼人工繁殖项目负责人。他的另一职务,是农业部下设的渔业资源监测站站长。据业内人士称,施是全国最熟悉长江刀鱼的人之一。 让我没想到的是,即便施的单位同意,施仍在一开始就拒绝了我的采访要求。“谁说我要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还没确定的事!你了解江刀,了解了又能怎么样?你以为你的一篇文章就能改变江刀的命运?我不想接受采访。”施有些不耐烦,然后借着有事,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吃了闭门羹的我没有气馁,开始与该所科研处的人接触,进行外围了解。对于生活在长江边的这些渔业科研人员来说,对江刀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作为普通人,亲身经历了美味的江刀由多到少,由贱至贵,由普通百姓盘中物到富者珍馐这一过程,另一方面作为专业科研人员,对这条鱼的命运有着或多或少的冷静深思。与他们的谈话,像闲聊一样有一句没一句地展开。这就是报纸采访的长处,受访者没有面对电视媒体那么有压力。 通过一个上午的“闲聊”,我基本知道了施炜纲拒绝我的真实理由,那就是科研人员认为,导致江刀日趋稀少的原因诸如江水污染、过度捕捞、产卵场破坏等,都不是学者所能左右的,在中国经济现阶段江刀濒临灭绝有其必然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学者是悲悯而无奈的,所以“欲说还休”。 又一个中午的闲聊后,我再次敲开的施炜纲的办公室,他仍然以同样的理由拒绝。我在他对面坐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我知道您是一个作事的人,江刀濒临灭绝的现状您是心痛的,但你又觉得无力改变。我知道,如您所说,我写一篇文章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作为一个记者,您作为一个学者,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都有责任有义务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我们人微言轻,哪怕没有作用……” 施眼中的不耐烦开始消失,打断我说,来采访的记者太多了,都只是了解一下刀鱼的简单情况,不痛不痒地在媒体上说几句,真的改变不了刀鱼什么…… 我接着说:“我的采访没有别的,就是要把这条鱼的真实现状,告诉社会,这是我为这条鱼唯一能作的,即使你不接受采访,我也会这样作下去。” 施的反问又开始了:“你是在作一个记者应该作的,但你曾讲过要问我刀鱼的人工繁殖问题,我问你,假如它在长江里灭绝的命运不可改变,人工繁殖的意义在哪里?你成功了,把它在池塘里养着,但江刀不洄游还是江刀吗?是的,可以把人工繁成功的刀鱼苗在长江中放流,但这是一项庞大的工作,不是一个科研单位或者长江边一个地市就可以作到的,这还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这不止是一条鱼的问题,甚至不只是一条江的问题,你能理解吗……” 正是在施的一系列反问中,我知道了我这篇文章应该写什么,那就是一条鱼背后的一条江。施的反问赢得了我对他的尊重,我的执着也赢得了他的认同,采访开始了。 施对我的帮助是巨大的,不仅有长江中下游江刀十余年间的观测资料,他个人对江刀命运的忧思,他还用自己“渔业资源监测站站长”身份,请江苏省常熟渔业观测站工作人员为我的采访提供方便。而正是在该站人员的帮助下,常熟渔民陈诸生一家才打消顾虑,允许我上船和他们到长江中捕捞江刀。而这,是这篇报道中的重中之重。 60多岁陈诸生出生于一个渔民世家,他甚至就出生在长江中捕江刀的渔船上,娶得也是一个捕江刀的渔民家的妻子,他的两个孩子是在捕江刀的渔船上出生的,他的生命与江刀就这样纠缠着。与他同捕江刀,我得以从一个渔民的视角去观察这条鱼的命运。 捕捞过度被学者指为江刀灭绝的重大原因之一。施炜纲认为,人类现在是在“拐点”之下毁灭性的捕捞江刀,他甚至提出了现阶段“禁捕”的说法。但陈诸生显然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几千年没捕光,这二三十年就捕光了?”他认为,起码像他这样正常捕捞不会让刀鱼灭绝,而一些网眼过密连小刀鱼的违法滥捕、前些年上游为获虾苗用密网封江,连江中最小的鱼都不放过等短视行为,才是罪魁。 陈诸生显然还是江刀濒临灭绝的受害者,他怀念二十年前一网下去几百上千斤江刀的快乐日子,而如今,鱼网越来越好,渔船越来越贵,鱼却越来越少。陈诸生显然有太多不能理解的东西。鱼儿,都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天问。 之后,我到上海、苏州和南京,分别拜访了数位关注刀鱼命运的学者,就这一天问继续求解。我发现,所有的讲述者,都带着施炜纲式的无奈。 在过度捕捞和污染之外,上海学者何为提出了产卵场破坏这一说法。他的依据是二十多年前南京大学学者袁传宓的一份“长江鲚属鱼生态研究”,该研究指出,江刀产卵场位于长江中水流缓处,多数在江水与支流交叉处。何为有些愤怒地说,这些河流交叉处现在几乎全建了水利工程,这些产卵场被大部分破坏,鱼儿都生不出来,怎会不濒临灭绝呢? 采访到最后,我发现事实上谁也讲不清楚造成江刀现状的根本原因。为什么讲不清楚,一定程度上是人类对自己作为食物的这条鱼,对于它生活的这条江,并不完全了解。 南京大学那位受人尊敬的老教授袁传宓已经去世,他当年作为“洄游人类”作出的“长江鲚属鱼生态研究”所能代表的,只是20多年前的长江生态。如今呢,江里的生态是怎样的呢?鱼儿生活在那里,快不快乐?或者,它们存活的空间,是在被怎样压榨并日渐缩小着?这些,如今有谁在关心呢?一江浑浊的水下,掩遮着多少与看似人类利益无关却与鱼儿性命攸关的秘密呢? 28年来,人类一直在试图对江刀进行人工繁殖,但一直没有成功。但正如学者施炜纲所讲,成功了又能怎样?这似乎又是一个与人类“吃”相联系的课题,而与江刀命运的关系,到底有多大呢? 稿件出来后,我给施炜纲老师寄去了一份报纸。在电话中,施说:祝贺你,写出一篇好稿子。突然,我觉得我也是功利的,我也是一个无奈的讲述者。 那张网,网住的是鱼,还是人类自己呢? |
 2007-12-06 23:35 2007-12-06 23:35
链接:
#3
|
|
 版主    组别: 版主 帖子: 13982 注册: 2003-05-31 编号: 18 |
拯救长江刀鱼28年败局
本报记者 宫靖 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报道 人工繁殖始终未获成功,人工放流恢复野生种群有待政府学界更多投入 中国水产科学院淡水渔业中心是国内刀鱼监测机构,由于渔获量锐减,该中心已无法统计2002年之后的江刀总体产量。 长江刀鱼濒临灭绝亟须拯救。 4月的一天,黄成老师走进自己工作的南京大学标本室,橱柜里30多个盛着福尔马林液的标本瓶里,长江刀鱼标本仍闪着银色的光芒。它们已经历了28年的岁月,如今依然为一届届学生所使用。 中国学者拯救长江刀鱼的努力始于28年前。1977年4月开始,黄成的导师袁传宓教授,带领4位同事日夜奔走在长江沿岸。他们的足迹正是在追随长江刀鱼洄游的路线。 袁传宓至今已辞世10年。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拯救江刀的行列,但至今为止,国内学界尚没有找到成功的路径。 第一次接触 71岁的秦安舲记忆中至今保留着南京的八卦洲(江中的一个小岛)捕江刀的美妙情景:1977年清明前后,南京江段江刀又肥又多,一网能拉出几百斤来,每个网眼里都有鱼,渔民得穿着橡胶皮裤下水收网。 那一年,国家刚恢复高考,她和袁传宓等几个南大的老师聚到一起,开始商量作一个课题。江刀很自然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长江下游的渔民最爱捕两种鱼,春捕刀鲚,就是长江刀鱼,秋捕凤鲚,就是凤尾鱼。但当时国内对长江鲚属鱼类的生态研究还是一个空白。”当时,科技部很快同意了几位鱼类专家的申请,国家自然基金先后拨出近6万元支持这个项目。秦安舲记得,项目负责人袁传宓为了让每个参与的人时刻记住自己肩负的责任,先是请一名油画家到长江里的渔船上转了几天,然后要求画家画一幅“4鲚图”———江刀、湖鲚(湖刀)、短颌鲚、凤尾鲚(凤尾鱼)。 课题组当时的思路是,想从科学角度为长江中鲚属鱼分类,并进行生态研究。“不用说,长江三鲜之首的江刀,是我们研究的重中之重。”这个项目前后进行了五六年时间,袁传宓带领着秦安舲和另外3名南大学者,每年春天随着江刀洄游路线跑。那时的江刀遍布长江沿线。这些“戴着大框眼镜”的人便自崇明口一直追到鄱阳湖、洞庭湖等流域。秦说,有人调侃这5个人是“洄游人类”。 “作这个课题的五六年里,袁教授和我们几个都发现,江刀的数量在明显地一年年减少,并且一年比一年瘦。 出于一种责任感,1981年,我们除了呼吁限捕江刀外,也开始着手作江刀的人工繁殖。 地点就在南京八卦洲。”由于科技水平有限,这次江刀人工繁殖没有成功,其过程也没有发表在任何刊物上,所以鲜为人知。但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人类第一次试图以人力改变江刀走向灭绝的命运。 停顿20多年后的新动力 上个世纪末一位朋友请客的午宴上,37岁的邴旭文再次吃到了幼时常吃的长江刀鱼。 这次吃江刀留给他的感觉很“怪异”:首先来自江刀的价格,一条2两左右的鱼在饭店里售价达五六百元;其次是江刀的味道,他第一次发现江刀真的很好吃。 邴和朋友谈起幼时吃江刀的事:几乎每个清明节,父母都会从最近的菜市场买回正宗且新鲜的江刀,就像现在买鸡鸭鱼肉一样普通。 但那时的邴,更喜欢肉大肉多一点的鱼。对20多年后花五六百元吃一条儿时不喜欢的鱼,他的感觉甚至是有些“愤怒”。 邴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科研处副处长、副研究员。今年初,他和同事等人向无锡市科技局申请立项,这个名为《长江刀鲚人工繁殖技术研究》的项目目前已被该局原则性通过,预计拨款30万元。 此前两年,上海水产大学、苏州大学有关江刀人工养殖的课题也已获批立项。 但此时,对江刀的研究已中断20多年。 2003年,长江中江刀产量已不足百吨。南京以上的湖南、江西和安徽江段,江刀早已形不成渔汛。袁传宓教授当年作出的翔实的刀鲚生态学调查,已和长江里刀鱼的现实情况相去甚远。 “如果后来有学者踩着老教授的足迹一直走下去,江刀的危机也许根本就不会出现。现在江刀快灭种了,社会才一窝蜂地来关注。”上海水产大学老师、“刀鲚人工育苗及养殖技术研究”课题组成员何为在电话中不住叹气。 多个项目获批,一个动力来自于长江水系多个鱼种人工繁殖的成功。 “螃蟹,1990年左右200来块1斤,现在也就三四十、四五十块了;对虾,1995年六七十块1斤,现在也就七八块;河豚,1999年左右300多块1斤,现在三四十块1斤。通过人工繁殖,这些水产品不都多起来了吗?江刀,能不能也搞人工繁殖?”邴旭文说到这些,眼睛会发出亮光。 邴并不是不知道20多年前袁传宓教授的失败,他还知道近年已经有学者再次失败了。但他依然很有信心,他的信心来自太湖银鱼人工繁殖的成功。 太湖银鱼在习性上与江刀很相像,同样是出水四五分钟就死,同样是人工繁殖一再遭遇失败。但近年太湖银鱼的人工繁殖成功了,并且具有放流增殖的可行性。“这就是说,从理论上看,江刀也有可能人工繁殖成功。” 难觅的性成熟亲鱼 但邴的同事施炜纲对江刀人工繁殖项目的看法是“无米之炊”。 施是该中心资源研究室主任、教授,最有可能成为无锡市江刀人工繁殖项目的牵头人。 “这个项目在理论上是有可能成功,但你知道吗,在江刀的繁殖季节,在长江里已经有多年很难找到性成熟亲鱼了。这让我怎么做得了?”坐在办公室里,施炜纲首先抛出了他的“牢骚”。 施的另一身份是农业部下设的长江下游渔业资源监测站站长,从安徽安庆江段到上海长江口到底有多少江刀,他显然是有发言权的。 性成熟亲鱼即指性腺发育成熟的江刀。资料显示,江刀最长寿命为4龄,它们一般在长江中的产卵场出生并发育成幼鱼后,游回大海育肥,次年性腺开始发育后再进入长江逆水洄游。洄游中水流的刺激加速江刀的性腺发育,最终它在产卵场产卵或排精。 “从理论上看,江刀每年都有一定的渔获量,那就一定有性成熟亲鱼存在,也一定存在产卵场。只要找到产卵场,就会捕到一定量的性成熟亲鱼,就可以搞人工繁殖了。但这几年,根据监测,长江中很少能捕到性成熟亲鱼。”施认为这是人工繁殖的最大难题。 为寻找性成熟亲鱼,上海水产大学老师何为几乎花了2年时间。 2003年四五月份,何为和两位研究生试图在距上海很近的江苏南通江段寻找,但通过解剖和切片观察,南通江段根本不可能有产卵场。 2004年,他们改变策略,顺江而上,决心不找到亲鱼绝不回沪。然而,靖江、南京等处带给他们的仍是失望。他们心一横,跑到南京以上江段寻找。 去年6月12日,在安庆渔政部门的帮助下,他们花500元在当地租到一条小渔船。第一网是在江中一个浅滩上下的,是空网。何为此时想起了南大老教授论文中江刀产卵场的特点,要求到长江边上的内河洄水湾处寻找。 “当时太阳很晒,我正无精打采地半躺在船舱顶上似睡非睡。突然,两个研究生惊喜地呼叫了,我一下子就爬起来了,立刻来精神了。那网我们捕到10来条江刀,有七八条是性成熟的亲鱼,并且有雌有雄……”事隔一年,何为在电话中的声音仍难掩兴奋。 在众多刀鱼的研究人员中,苏州大学农学院水产系陈剑兴老师有着同样的“幸运”。 从2004年3月开始,他频繁来往于常熟至张家港江段。终于在6月中上旬,他同步网到了性成熟的雌雄江刀。 陈剑兴和何为一致的看法是,要在长江中捕性成熟的亲鱼太难了。想同时捕到雌雄亲鱼,更难。想捕到科研所需的量,则是“难上加难”。 咖啡杯里的奇迹 2004年6月13日,找到性成熟亲鱼后的何为再次上船。一大早上船前,他在一户渔民家和渔民一起追赶一只鸭子,最终拔到了一根鸭毛。他还买了几只透明的小咖啡杯。 “这些可能是世界上最简易的人工繁殖工具了”。何为笑言。 江刀是通过体外授精繁殖后代的物种之一,产卵时雌江刀将卵排在水中卵场,而雄江刀也将精液排在卵场。江水会将江刀的精卵自然融合。而人工授精的方向,就是尽量模拟自然授精的环境和过程。分别挤出卵液和精液后,用羽毛轻搅,使卵和精子调均,再加入新鲜的长江水。 早7点,渔船又驶进长江。第一网在1个小时后出水,有10来条亲鱼,雌多雄少,何为和学生把所有雌鱼的卵液都快速挤在杯子里,再把眼泪一样少的雄鱼精液挤入。然后加入新鲜的长江水,放在阴凉处。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时间。 施炜纲,最有可能成为无锡市江刀人工繁殖项目牵头人的学者。 秦安舲,国内较早关注长江刀鱼生态的学者。 何为没敢拿出那根好不容易拔到的鸭毛,他担心毛的黏性浪费掉宝贵的精液。 “我们挤了4个杯子。一直忙到下午两三点钟,才发现早过了吃饭时间。”据何为观察,杯内注水几秒钟后,卵和精液都浮在了水面上。半小时后可以看出,水面上有些卵仍呈半透明,而另一些卵则发白了。仍然透明的就是受精卵。4个杯子中,有3个受精率为10%左右,一个杯子则有一半左右。 何为留下了那个受精率有一半的杯子。半个多小时后,这个杯子被放置在何为宾馆房间的小桌上。几乎每隔几分钟,何为就要观察一次。 一天多后,何为对着杯子拼命揉自己的眼睛,没错,他的确看到那些受精卵在微微地动。何为知道,那是胚胎在动。第二天,几十条半透明的鱼虫般大小的鱼苗开始破膜,并拖动着卵囊开始间歇性地游动。 由于没有任何充气和孵化工具,第三天,几十条小江刀苗死去了。但何为认为,他已经看到了人工繁殖江刀的曙光。 与何为几乎同时捕到性成熟亲鱼的陈剑兴则未能看到江刀苗。3次人工授精均告失败。他认为这有3种可能:1、雌雄性成熟可能没同步。2、雄鱼精子可能没有活性。3、雌鱼卵子可能还不够成熟。 何为还无法解释自己此次“成功”的原因。他告诉记者,从见到鱼苗到宣布人工繁殖成功,还有很远的距离。 见苗后还有多道重要关卡,比如卵囊消耗光后鱼苗能否顺利开口进食,随后能否顺利实现膘充气,还有能否顺利度过平游期,在这些之后,还要度过仔鱼、稚鱼阶段。只有最终达幼鱼阶段,才算是人工繁殖成功。 “但毕竟我们已经看到曙光了”。何为说,自己回到上海后,第一件事就是做了一个直径20厘米的有机玻璃孵化器。今年5月底,他将再次上船。 人工养殖的“老头”鱼? 去年下半年,在南通一个四面临水的“江心洲”,上海水产大学课题组把四面围起,只留很少的口专门开闸“等鱼”。在涨潮的七八月份,不少“迷路”的小江刀会自动闯进研究基地,这时候,再将闸门关闭—————最终,5000尾江刀幼苗被“骗”进基地中进行人工养殖。 这种方法被叫做“灌江纳苗”,是目前惟一有希望成功的人工养殖刀鱼的方法。 江刀一大特点是出了江水四五分钟即死。上海水产大学鱼类研究学者唐文乔曾试图把江水注入桶中,并辅以换气设备,但即使这样,接受试验的江刀仅仅存活了8个小时。 学界目前的思路是,人工繁殖假使成功,下一个问题是实现江刀人工养殖。而人工养殖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江刀能在养殖环境下性成熟,并且产下第二代。 2003年4月,江阴市也有一水产单位宣布江刀灌江纳苗成功。这些江刀现在已是3龄鱼,体形已像大鱼,但人们尚未观察到它们性成熟。 “没有水流的刺激,人工养的江刀性腺也许永远不可能发育成熟,极有可能成为老头鱼。”邴旭文说,这是人工养殖中亟须突破的难题。 放流的可能性 学界无法回避的另一个质疑是:即使江刀顺利地实现了人工养殖,普通百姓可以从菜市场买回池塘里产的大量刀鱼了,但这些不再回到大海,不再参与洄游的刀鱼,还能是那个长江三鲜之首的江刀吗? 施炜纲认为不可能,他的理由是不参加洄游的太湖湖刀、古长江河道中的石首刀鱼,味道远不如江刀,刺多,体形也偏小,食用价值不大。“人工养殖的池中之物,不可能比它们更好,因为它活动的区域更小了。”“即使人工养殖成功了,对长江里的刀鱼种群又有多大意义呢?”施炜纲毫不掩饰自己对人工养殖刀鱼项目的“抵触”情绪。 一个可做类比的例子是,同样名列“长江三鲜”的河豚人工养殖搞成功了,但长江里的野生种群仍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 上海水产大学鱼类研究学者唐文乔说,河豚的野生数量之少远比江刀严重,只是因为它的人工养殖成功了,价格下来了,渔民认为捕河豚划不来,才放下屠刀,让这种鱼在长江中能保有微小的数量。 “从道理上来说,河豚的人工养殖、繁殖已成功,在长江中对河豚放流增殖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但实际上是不会有人做这样的‘傻事’的”。 唐文乔解释说,长江是公共水体,放鱼的人不一定能再捕到这些鱼。因此,河豚人工繁育成功已有10余年,但至今没有人组织过从生物多样性角度出发的生态意义的河豚放流。野生河豚的命运,可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 一些学者认为,即使不考虑经济效益,人工放流也有实现的难度。 陈剑兴估计,一条性成熟的雌刀鱼约有1万个卵年春天随着江刀洄游路线跑。那时的江刀遍布长江沿线。这些“戴着大框眼镜”的人便自崇明口一直追到鄱阳湖、洞庭湖等流域。秦说,有人调侃这5个人是“洄游人类”。 “作这个课题的五六年里,袁教授和我们几个都发现,江刀的数量在明显地一年年减少,并且一年比一年瘦。 出于一种责任感,1981年,我们除了呼吁限捕江刀外,也开始着手作江刀的人工繁殖。 地点就在南京八卦洲。”由于科技水平有限,这次江刀人工繁殖没有成功,其过程也没有发表在任何刊物上,所以鲜为人知。但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人类第一次试图以人力改变江刀走向灭绝的命运。 停顿20多年后的新动力 上个世纪末一位朋友请客的午宴上,37岁的邴旭文再次吃到了幼时常吃的长江刀鱼。 这次吃江刀留给他的感觉很“怪异”:首先来自江刀的价格,一条2两左右的鱼在饭店里售价达五六百元;其次是江刀的味道,他第一次发现江刀真的很好吃。 邴和朋友谈起幼时吃江刀的事:几乎每个清明节,父母都会从最近的菜市场买回正宗且新鲜的江刀,就像现在买鸡鸭鱼肉一样普通。 但那时的邴,更喜欢肉大肉多一点的鱼。对20多年后花五六百元吃一条儿时不喜欢的鱼,他的感觉甚至是有些“愤怒”。 邴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科研处副处长、副研究员。今年初,他和同事等人向无锡市科技局申请立项,这个名为《长江刀鲚人工繁殖技术研究》的项目目前已被该局原则性通过,预计拨款30万元。 此前两年,上海水产大学、苏州大学有关江刀人工养殖的课题也已获批立项。 但此时,对江刀的研究已中断20多年。(来源:新京报) |
 2007-12-06 23:40 2007-12-06 23:40
链接:
#4
|
|
 版主    组别: 版主 帖子: 13982 注册: 2003-05-31 编号: 18 |
看完真不知道说什么,中国人的悲哀!
|
 2007-12-07 03:21 2007-12-07 03:21
链接:
#5
|
|
|
中级会员    组别: 正式会员 帖子: 6162 注册: 2003-06-10 来自: 厦门 编号: 54 |
呼呼大睡
-------------------- mail:yunlihe2004@163.com
电话: 15980809930 |
 2007-12-07 06:13 2007-12-07 06:13
链接:
#6
|
|
 资深掺和者    组别: 正式会员 帖子: 10919 注册: 2005-06-26 来自: 厦门 编号: 882 |
读罢泪两行!
-------------------- 给我一双彩虹的翅膀,我要飞向那自由的天堂。
微信公众号:山鹰的自然行记 |
 2007-12-07 18:17 2007-12-07 18:17
链接:
#7
|
|
 资深会员    组别: 正式会员 帖子: 506 注册: 2005-08-08 来自: 漳州芗城区 编号: 956 |
很感人啊,看了一篇就看不下去了
-------------------- Rom 1:20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
 2007-12-07 22:25 2007-12-07 22:25
链接:
#8
|
|
 版主    组别: 版主 帖子: 13982 注册: 2003-05-31 编号: 18 |
中国软壳龟,危机的象征
【打印】【关闭】 来源:纽约时报 日期:2007-12-6 18:14:05 访问量:6 五十年来,这只披着褪色的、坚韧的壳的雌性龟不受人注意,也没有人欣赏,但如今却变成长沙市那衰落的动物园的贵重物品。她被喂以生肉特餐。她小小的池子已经装上了防弹玻璃。摄像头监视着她的举动。夜间有警卫站岗。 议程很简单:这只龟一定不能死。 在今年年初,科学家认定她是地球上已知的最后一只雌性的长江大软壳龟。她大约80岁,体重近90磅。 恰好,地球上还有唯一一只已知的、无可争议的雄性。他生活在苏州的动物园里。他大约100岁了,体重约200磅。他们是拯救一个物种的希望。据说,这个物种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龟。 曾帮助拯救这个物种的美国龟类专家佩里特查尔德(Peter Pritchard)表示,这是非常可怕的情况。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龟象征着健康长寿,但最后两只长江大软壳龟的传奇不如说是中国野生动物和生物多样性情况危殆的象征。污染、狩猎、无节制的开发在摧毁自然栖息地,并危害植物和动物。 中国包含了世界上最丰富的一些生物宝库,但对动植物最新的大调查揭示了在过去十年,本来就黯淡的局面变得更加黯淡。科学家表示,如今中国的哺乳类物种有近40%濒临灭绝。至于植物,情况更为严重;70%不开花的植物物种以及86%开花植物物种被认为情况危殆。 最大的问题是对土地和水源的激烈竞争。中国到2020年经济翻两番的目标意味着工业、不断扩张的城市、农民要争夺有限的可用土地。城市和工厂常常为扩张而争地;而农民则要开垦本来可能是栖息地的土地。据调查,中国已经失去了一半的湿地。 对于试图扭转局势的中国科学家和保育人士来说,首先面临的挑战是说服政府把保护野生动植物当作重要的优先事项来对待。数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领导人强调对自然的统治,而不是强调与自然共存。动植物仍然常常被视为具有食用或药用价值的商品,而不是自然秩序的必要组成部分。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Lu Zhi)表示,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整个概念在文化中是新生事物。 科学家表示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重要中心的地位令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的状况备受全球关注。中国许多物种集中在多山的西南地区——有时远及西部的香格里拉——以及西藏、海南岛以及和与朝鲜交界处。濒危的土著动物包括大熊猫、几种山鸡和猴子,还包括包括鼩和啮齿动物等以及一系列小型哺乳动物。 中国有庞大的自然保护区系统,主要在该国较为偏远的西部,但资金筹措的水平甚至远低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保护计划中被认为最成功的就是拯救大熊猫的工作。如今大约有2000只熊猫生活在熊猫保护区。其他人工繁殖计划帮助扬子鳄和藏羚羊脱离灭绝的边缘。 但与那些被忽视并逐渐灭绝的物种数目相比,这些成绩并不突出。去年,长江白暨豚被宣布灭绝。 |
 2007-12-08 01:12 2007-12-08 01:12
链接:
#9
|
|
 普通会员    组别: 正式会员 帖子: 2970 注册: 2004-10-17 编号: 545 |
好文~有时间一定好好拜读!
谢谢岩鹭转贴进来~ -------------------- 生命就在于折腾~
--鸟会最外行-就是我的专长 |
  |
1 位会员正在阅读此主题 (1 位游客和 0 位隐身会员)
0 位会员:

| 简化版本 | 当前时间: 2025-10-05 18:15 |
Powered By IP.Board
© 2025 IPS, Inc.
Licensed to: ©2006-2007 厦门观鸟会,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