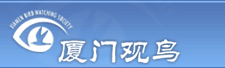|
 2010-02-13 09:17 2010-02-13 09:17
链接:
#1
|
|
 版主    组别: 版主 帖子: 8911 注册: 2003-05-31 编号: 12 |
保护区的很多活动是经济活动——访动物行为学博士约翰·马静能

约翰·马静能长达14年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主席。 1947年出生的他,走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的植物园里,健步如飞。偶尔,他会在一棵老松树下停下来,仰头举起相机,对着高高的树梢转换角度接连按下快门。如果不是在事后看到他相机里那些鲜见的鸟儿,一般人无法了解他在拍些什么——那些羽毛黄、绿相间,在树枝、树叶间隐藏得很好的鸟儿,似乎只有他那经长期训练而成的特别敏锐的眼睛才能捕捉得到。他开玩笑称自己为“鸟人”。不仅如此,他还能够在百兽嘈杂的大森林里,靠耳朵听闻的细微声音迅速感知红猩猩的方位。他模拟动物的叫声特别惟妙惟肖,堪比相声中的口技。 他是第一个到越南工作的西方生物学家,把WWF的物种保护项目带到了越南。在越南和老挝边境,他发现了体积庞大的剑角牛,被誉为“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 在过去100年里,人类新发现的哺乳动物总共只有10种,3种和他有关。他曾在原始森林里和大象、熊搏斗都没有受伤,右手缺失的小拇指是他向往的野性力量40年来惟一在儒雅、清朗的他身上留下的小小警告。 国际知名生物保护专家约翰·马静能(John MacKinnon)长达14年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主席,现为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宣传教育子项目负责人。在英国总领馆文化教育处日前在昆明举办的“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媒体研修班讲座间隙,记者采访了这位集著书、制片等多种才能于一身的动物行为学博士。 问:您曾与著名动物生态学家珍妮·古道尔一起在非洲考察黑猩猩等野生动物。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马静能:我舅舅曾经在肯尼亚政府部门任职,认识当时正在非洲工作的珍妮·古道尔。大学毕业后,我让舅舅帮我找一些可以去非洲的项目,他就把我推荐给了这位老师。遇到珍妮·古道尔之后,我还从她的丈夫——《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位摄影师身上学到了很多摄影技术。 问:您对野生动物的兴趣是与生俱来的吗? 马静能:我有4个姐妹,她们都喜欢养宠物,但我不喜欢这类可爱的小动物,我从小喜欢可怕的野生动物,像蜥蜴、老鹰、蛇之类的。在我12岁的时候,英国有个NGO为鼓励年轻人接近大自然,举办了一些夏令营活动。我去参加了3次,听了一些有关地质、自然生态方面的讲座。这样,其实在13岁前,我就对大自然有了不少了解。上大学时,我非常喜欢自然历史,一心想去自然保护区工作,向往怀着孩子般的心情,去体验发现的喜悦。但现在,我也知道了其中的危险。 问:谈谈你发现Saola的经过吧。 马静能:上世纪90年代初,我正负责WWF与IUCN的一个项目,在越南和老挝边界长山山脉的一个小村庄里工作的时候,看到了一种很奇怪的角,追查之下发现那是一种长得很像羚羊的野牛的角。这种野牛(当时以发现地为其命名为“Vu Quang Ox”,后来改用越南当地的名字“Saola”)以前从未被发现过。在 20世纪末居然还能出现大型有蹄动物的新种,这在当时成了轰动全球自然保护界的大新闻。其实,《东南亚鸟类图鉴》的编者Craig Robson在1980年代末也到过那一带,当地人也给他看过一些很怪的角,但当时他认为那是山羊角,没有加以重视,后来他肯定那时看到的就是剑角牛的角时,简直后悔死了! 问:听说您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86年。当时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状况是怎样的? 马静能:当时中国只有300个自然保护区,还没有相关的NGO,也没有任何介绍鸟类、禽类的书籍,大多数中国生物学家跟着俄罗斯生物学家采集标本,主要研究一些有经济价值的动植物。 问:这二十多年里,您在中国开展了哪些工作? 马静能:二十多年里,我呆在中国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我编了一本介绍鸟类的中文书籍——《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其中包含了1288种野生鸟类,并附有很多图片向读者介绍如何识别鸟类。这本书现在被许多观鸟团队使用。去年我编了一本关于中国哺乳动物的书,在其中收集了488种哺乳动物。事实上,对小型哺乳动物的识别比对鸟类的识别更困难。你要把它们逮住,近距离地观察其牙齿、身体结构等。在中国,光鼠类就有三十多种。 问:您提到环保人士要选择合适的场合向公众传递自己希望传递的信息,能否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吸引公众对那些陌生野生鸟类的注意力的? 马静能:比如,在中国南方、泰国和越南境内有一种濒临灭绝的鸟,我说出它的名字你肯定就能记住它。它叫“mother-in-law bird(丈母娘鸟)”。相传有一个男青年很讨厌他的丈母娘每天中午睡觉时打鼾的声音。有一天中午,丈母娘又鼾声如雷,男青年实在忍不住了,就拿了把斧头去砍他们住的木房子的桩架。丈母娘鸟的得名就因为它的叫声像斧头砍木桩发出的声音:笃,笃,笃,笃…… 问:您虽然是个鸟类学家,但似乎一直非常关注生物多样性问题。 马静能:物种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就像许多本同种书和由一批不同的书组成的图书馆的关系,其所包含的知识价值是不同的。生态系统就像一幢房子,其门、窗等部件被取走得越多,房子就越脆弱。 在英国,有一种蜜蜂是非常适应寒冷气候的,但全球变暖之后,它们只能往北迁移,越过苏格兰再往北,它们就只能掉到大海里去了。所以,现在它们已经濒临灭绝。北美、欧洲的一些蜜蜂则因体内生寄生虫而死去。在中国四川地区,苹果树因为缺少蜜蜂而需要人们搭着梯子为其进行人工授粉…… 人们可能没有想到,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每年预计高达16万亿至6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10%。对于生物多样性的投资回报可高达成本的300倍,没有任何一桩生意可以有这么高的投资回报率。 问:在中国,您看到了哪些对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利的现象? 马静能:中国和印度不太一样。印度很脏,人们对自己的外观也不太注意,但在印度,到处都有鸟,哪怕是在尘埃中飞翔。猴子也会进到人们住的屋子里偷东西。因为印度人信佛教,比较尊重大自然,提倡素食,不怎么吃动物。中国虽然在过去,道家也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但这些信念现在受到了商业化消费的冲击,给自然保护带来很大的压力。要让人们珍惜自然,也许得从娃娃抓起。 我去年夏天去了趟北京的动物园,看到许多游客对着兽笼大叫,向动物扔矿泉水瓶等东西迫使它们作出反应。很少有关于那些动物的具体介绍。这样,去动物园也不能形成人们对动物的良好态度。动物园现在更关注的是怎样把房子修得更漂亮,吸引更多的游客,靠门票挣更多的钱。在香港,去动物园是免费的,这是政府的责任——为了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动物。 问:听您这么说,最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好像还不是科技。 马静能:自然保护其实是一种人际关系的调整,与科技没有多大关系。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年轻的生物学家对实地考察不感兴趣,喜欢用一些高科技手段(如:DNA检测等)来开展研究,我称这为“还没有学会走路就想跑”。他们用高科技只是为了炫耀,而不是真正出于保护生物的目的。我从前还是个IT专家呢,但我并不觉得高科技在物种保护中有多重要。科技的应用有时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不再关注一些根本的东西,就像计算机可能会摧毁我们的生活。但即使没有电脑、GPS、远程控制系统,也可以很好地开展保护,人们首先应该做很好的观测和记录。 问:您觉得目前中国的保护区做得怎么样? 马静能:现在中国大约有2000个自然保护区,每个保护区有近200名工作人员。他们每天在保护区里到处走动,但很少有人能够把自己观察到的东西详实地记录下来。很多保护区的设立并不是因为人们真正认为它们值得保护,保护区的很多活动还是经济活动。中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要对生物进行很好的观测和记录,先要很好地了解物种,所以我编了关于鸟类和哺乳动物的书,但其它物种的相关书籍仍然缺少。应该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项工作中。有时,新的信息不断出现,你需要不断地对旧有信息进行调整,事实虽然是事实,但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所有的真相。 摘自【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41131 -------------------- 手持AK,深入丛林。乘风破浪,一如既往!......
Che! --- http://photo.qianlong.com/4505/2003-5-29/182@870066.htm |
 2010-02-13 10:23 2010-02-13 10:23
链接:
#2
|
|
 资深掺和者    组别: 正式会员 帖子: 10919 注册: 2005-06-26 来自: 厦门 编号: 882 |
坚定了咱们厦门鸟会坚持常年做调查的决心啊!
原来剑角牛也是马静能博士发现的,真是太牛叉了! -------------------- 给我一双彩虹的翅膀,我要飞向那自由的天堂。
微信公众号:山鹰的自然行记 |
 2010-02-14 10:03 2010-02-14 10:03
链接:
#3
|
|
|
会员    组别: 版主 帖子: 2724 注册: 2004-11-08 编号: 587 |
我编了一本介绍鸟类的中文书籍——《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其中包含了1288种野生鸟类,并附有很多图片向读者介绍如何识别鸟类。这本书现在被许多观鸟团队使用。去年我编了一本关于中国哺乳动物的书,在其中收集了488种哺乳动物。 想看看马博士编写的哺乳动物的新书 当当上有: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732063 -------------------- 观鸟会-我们的精神家园
|
 2010-02-14 11:56 2010-02-14 11:56
链接:
#4
|
|
 资深会员    组别: 正式会员 帖子: 1103 注册: 2008-11-11 编号: 4086 |
坚持就是胜利
|
 2010-03-23 16:41 2010-03-23 16:41
链接:
#5
|
|
 新鸟入门  组别: 注册会员 帖子: 32 注册: 2008-10-22 编号: 4021 |
啥时候中国人能写几本像马敬能博士写的那样的书呢?
-------------------- 我叫“老鹞子”,一个自然的,特别是鸟儿的记录者,还有一个常用的ID是“sanpatrick”
|
  |
1 位会员正在阅读此主题 (1 位游客和 0 位隐身会员)
0 位会员:

| 简化版本 | 当前时间: 2026-02-12 12:40 |
Powered By IP.Board
© 2026 IPS, Inc.
Licensed to: ©2006-2007 厦门观鸟会, 中国.